在法国读新闻:苦海无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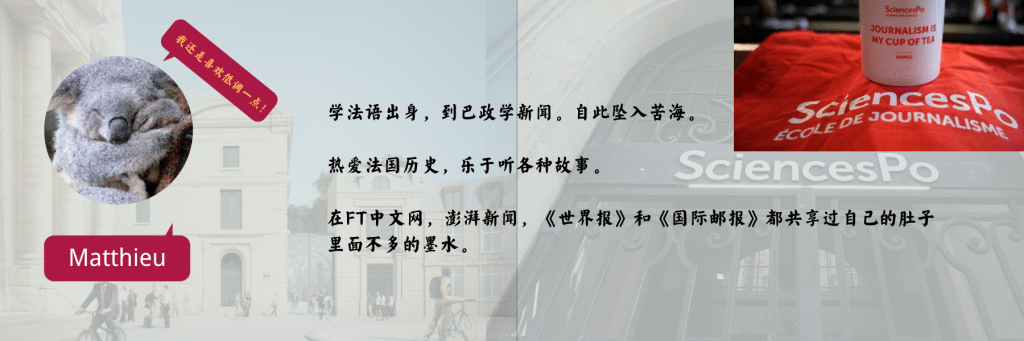
“我不再希望有人仅仅凭着一份热情来法国学新闻 ,”在一声叹息后,来自浙江的Cloé又以很快的速度拨通了下一通电话,在短暂的介绍过自己的身份和电话的目的后,短暂的对话以“祝您新的一天顺利”结束。很明显,电话另一端的联系对象又一次拒绝了她的采访请求。“这是家常便饭吧,失望是肯定的,不过也没什么太多时间失望吧,毕竟作业是肯定要交的”,她又继续投入工作中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法国新闻专业学生的日常,一天的课程从早晨九点开始,一直到下午六点。不过,具体的结束时间谁也说不定,兴许老师要是讲的兴起,到家的时间在晚上八九点也算是家常便饭。
除了课程的长度之外,课程的强度可能是“更大的问题”。在她就读的在法国排名第一的新闻学院里尔高级记者学院学校(École supérieure de journalisme de Lille, 简称ESJ Lille),一般的要求是一天一篇报道,这意味着在一天内要完成新闻采编的全部。从确定选题,联系采访对象,完成采访再到整理采访内容完成报道,这一切,都要在短短的一天之内完成。如果要是对于电视或者电台的新闻报道,这还要加上往返报道现场以及后期剪辑、配音的时间。

“即使是在有着丰富资源的媒体中,有的选题也不可能在一天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别何况是对于我们这些学生们来说了,”Amélie作为一名国内从首屈一指法语本科的毕业生的她,在ESJ度过的两年中,也无数次遇到这种问题。“如果法国学生还愿意在老师面前争辩一下自己遇到的问题,对于国际学生来讲,老师可能都不愿意听吧。”在两年的新闻硕士结束后,她选择回到国内在一所大学教授法语。
相比较起国内的新闻专业,法国只有在硕士学段才设有新闻专业。而在芸芸新闻学院中,又以其中十四所被行业认可的学校最为出名,为了进入其中学习,大多数申请人都会花费将近一年的时间来准备入学考试,更有其中不少为了能够在一所认可的新闻学院中谋得一席,不惜复读或者报名专门的集训班。以雷恩政治学院的新闻硕士为例,即使是作为一所并不被行业认可的新闻学院每届也只招收15名学生,而据学院的负责人克里斯多夫·詹贝尔(Christophe Gimbert)介绍,每年学院都能收到超过四百份申请。而在像ESJ Lille这样即作为行业认可,而且在各类排名中尝尝占据榜首的新闻学院来说,每年收到1000份申请材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而至于每年的录取数量则50多人。
“我们只能保证国际生能听懂学校的课程”
不过,每年ESJ的学生数量都稳定在60人。至于,剩下的生源则来自“国际生通道”。在法国十四所认证的新闻学院中只有里尔高级新闻学校以及巴黎政治学院的新闻学院(École de journalisme de SceiencesPo)招收法语项目国际生。这两所其中又以ESJ Lille招收的数量最多,每一届的招收数量不超过10人。
不过相比较其法国学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竞争,通过国际生间的申请却远没有如此激烈。不管是在巴政的新闻学院还是在ESJ,针对国际申请者的考核只有面试。而法国学生的录取过程,则要更复杂得多,不仅从刚开始的材料关就会刷掉不少申请者,在面试之前还有一次笔试,考察申请者对时事热点以及基本新闻的写作能力。
纵然国际生相对于法国学生有着“天然不足”,不过也无法解释在录取标准上的差异。有一位只在法国读过一年语言班的国际生也曾被ESJ录取。而在今年的录取过程中,ESJ对国际生的录取过程中加强了材料审核,加入了若干道问答题,考察申请者准备情况。根据澎湃新闻获取到的一份申请者材料,这为来自非洲的申请者在其中一道模拟采访题中提出自己希望采访法国国际电视台France24驻其国家的特派记者来了解当地的疫情最新情况。对此,雷恩政治学院新闻硕士的负责人克里斯多夫·詹贝尔在接受采访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很奇怪,我并不理解为什么这为申请者认为一个特派记者能够比当地的卫生官员或者当地的医务工作者更了解当地的疫情。”此外,这份申请材料中也有不少法语语法以及标点符号使用上的错误,即使申请者有着两天的时间来完成问答的部分。而最终,在经过面试后他成功的进入了ESJ的硕士项目。
“某种程度上,我自己本身也是国际生通道的受益者,但如果把标准放得这么低的话,这和郭德纲相声中那个‘管杀不管埋’的梗有什么区别呢?”目前在读的中国学生Matthieu讲到,即使从高中就开始接触法语,即使与这门都德眼中“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打了八年交道后,面对法国新闻业对拼写以及写法的要求,也时常招架不住。
而这所从1924年建校就接受国际生的新闻学院在国际学生培养方面也有着自己的目标:在毕业后让他们回本国工作。据Cloé提供的信息,ESJ的教务主任就曾向她讲过,学校招收国际生的目的就在于:“我们招收国际生的标准只保证他们可以听懂课程,至于是不是能够工作我们无法保证,我们培训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他们可以回国工作。”只不过看起来很正确的道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变了味儿”。
Amélie则回忆到,在之前研一与研二之间选专业方向的时候,学校的负责人就曾经打着“为你们好的”的旗号尽量将希望专攻电视新闻的国际生规劝到纸媒方向。在研究生第二年根据传播介质而分成四个专业方向中(包括电视、广播、纸媒以及网络媒体),除了电视之外,国际学生在广播和纸媒方向的竞争力只会更低。相比较起对发音要求很高的广播,亦或是对写作水平要求很高的纸媒,对剪辑技术以及摄像机使用技术要求较高的电视新闻可能是能够规避自身先天性不足为数不多的出路之一。“大概就是不希望国际生抢法国人的位置吧,给法国人自己的位置都不够,就更别提说是给国际生了”Amélie冷笑了一下。
当然,兴许对于国际生来说唯一比法国学生高一点的地方就在于学费了,相比较起可以享受本国政府提供的各类奖学金的法国学生,以及根据父母收入而计算得出的阶梯学费政策,国际生不论出身,都需顶格缴纳学费。而目前由于法国政府以及法国高教署不提供对新闻专业对应的奖学金,就读的国际生需要自行承担学费以及生活费。哪怕是针对中国学生,作为中法建交50周年由中国驻法使馆设立的 «Français excellent »奖学金也目前合并到埃菲尔奖学金下。当然,根据不少国际生的描述,面试中避不开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学费由谁来支付呢?”
“融入,可能时间长了也就不那么在乎了吧”
ESJ校长在给一位国际生家人的邮件中提到:“与法国学生比较起来,国际生融入的路径有所不同,但绝不意味着这种融入是不可能的”。只不过要比不少人所想象到的“要难很多”。
法国记者学院的学制一般为两年,第一年进行基础的课程培训,第二年根据个人意愿进行专业方向的学习。尽管各个学校的区分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不过基本上都是面对广播、电视以及更加传统的纸媒以及近年来新兴的新媒体。在学校中进行各种报道,始终绕不开的一道坎就是:找搭档。“我倒是更希望老师直接安排搭档,要不然我自己找搭档的话,大概率就是最后才能找到搭档。”在巴政新闻学院就读的Matthieu这样形容自己找搭档的经历:找一个善良的法国人。“组队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想到国际学生,可能到最后都分剩下了,大家才会想到要把你加进来吧,”Amélie说到。
至于语言问题,Matthieu更愿意将其比作“无形的天花板”:“我能做的就是把这片天花板不停地向上推,尽量的减少它带给我的影响,至于是不是真的有一天能够突破这种局限,我不敢打包票。”不过对于这些大部分法语本身就是非母语的国际生来讲,在写作水平上被人指摘还能说得过去的话,学校里面有些针对法国同学的遭遇可能更能引起他们的共鸣。
学校的老师会批评甚至直接嘲笑非洲同学的法语,而这些的母语正是法语,Amélie回忆到。而Cloé也提到自己一个在美国读本科的法国同学也被老师讽刺“法语不够好”的情况。“我觉得原罪不一定是他们的法语水平问题吧,兴许是在于我们的出发点就不同,如果我是一个外国人,老师不会去试图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因为他们天然觉得一个非母语的法语使用者其法语就是不完美的,”Matthieu感叹到。
笔者向ESJ申请采访,希望可以就以上细节获得校方的说法。在采访请求发出若干天之后的一个周日晚上,临近凌晨笔者得到了对方的邮件回复。先将具体回复的内容放在一旁, 短短两句话的回复用了两个几乎只有在法国学生上课速记才会用的缩写。
法国新闻强调观点,要求记者有着鲜明的观点,用中国的话语体系来说就是:坚定立场。在一次作业中Cloé就经历到了这样的情况。今年三月底法国左派大报《世界报》(Le Monde)针对CGTN发表的一篇社论提出质疑,认为社论的匿名作者并“不存在”。而仅在一天后他们的同行,同属左派的《解放报》(La Libération)记者经过求证发现这一记者真实存在,只不过由于其个人原因,暂时不持有法国的记者证。后者披露的信息迫使《世界报》在之后修改了自己的文章,并将标题修正为:《围绕CGTN的一篇文章的争论》,来回避自己当初的失误。
Cloé在一次广播报道的课程中试图将这一事件加以解释,指明《世界报》起初报道中的错误。而最后,在她老师的指导下报道最后成了为《世界报》记者“开脱”:“我的广播老师和我讲,‘记者不可能是全知全能,只要他调查的过程没有问题,那就称不上是错误,只能说是失误。’可是,如果仅仅凭借一个人没有记者证就说一个人不是记者,即使在法国媒体圈子内部都不一定能够说的上是一个站得住脚跟的理由。”
“真正有能力的人,都换行了吧”
Nicolas在法国完成两年的新闻专业的学习后选择了前往欧中一所商学院进修,之前希望成为一名记者的他现在的目标是进入一家投行。“这个圈子过度的以法国人为中心,外国人太难进入了,”他感叹道。这种以法国人为中心的趋势不光表现在记者的聘用上,更体现在价值观上。
Matthieu在《世界报》的实习过程中适逢国内有关整顿教培产业风声越来越近的五月,他一直向自己的实习主管提出这个选题,希望可以得到机会完成写一篇与中国育儿压力有关的选题,不过一方面是“这个题非常有意思”的回复,另一方面则是:“我们还希望等一等更新的选题。”而一直等到他实习结束的五月底,他也没能等到机会。在他离开时,得到了他上司的一个简短的承诺:“我们会写出来的。” 而这篇文章最终出炉却要等等两个月后的八月份,而切入点却早已和他当初提的大相径庭:中国整顿教培产业,引起企业股价腰斩。“最终文章还是落到了中国经济上面,但在中国除了中国政府以外还有十三亿中国人,我们讨论中国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能多讨论有关中国人的故事呢?”Matthieu不禁提出这样的疑问。
不过即使是挨过了两年的学校,就业也并非易事。大部分刚刚从新闻学院的学生都不会直接拿到自己的终身合同,都要在圈子里面“摸爬滚打”几年,有了一定经验后,媒体才会考虑开出长期的工作合同或者终身制合同。这一惯例对法国人可能不是什么问题,但对持有非欧盟护照的国际学生又进一步限制了他们的选择。
Catherine在毕业后给法国电视台France24做了一年摄像记者,她的合同大多是以几天为限,有的合同实现甚至只有一天。“最后光是合同纸摞起来就挺高的了,”她打趣到。不过这样短期的合同却无法作为申请工作签证的依据。她也只能在一年之后选择离开France24,以自由职业的身份在法国工作。
此外,她也给国内一些媒体撰稿,拍摄短视频。在新冠疫情到来之前她回到了国内,在国内媒体圈摸爬滚打一圈后她目前在广告业工作。最近她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变成了:“广告行业多好啊,没那么累,挣得还比新闻多。”
“留学本身就是一个祛魅的过程,”Matthieu总结道。这些来到法国的学生有的是为了能够通过新闻学习见到更多的人,更深入的了解法国;有的则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大家更好的了解中国,还有的则是单纯为了能在法国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
兴许有的人中途退出,不过继续留在这条路上的人们还在为着自己的目标继续前进。Cloé目前正在准备自己的实习,Matthieu则开启了自己的留学咨询服务,用他的话说,他希望后来的人“可以少走弯路”。
(图片来自网络)
以下为本站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