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哲学家和名酒庄主在一起喝酒时,他们会聊些什么?
—记法国哲学家拉斐尔·昂多凡与勃艮第名酒庄主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的一次“跨界”交流……
“酒醉是一种对某些人们平常所忽视的事物给予关注的方式(……),是一个最美的话题;全部赌注在于恰到好处地酒醉,让头晕转而不昏头(avoir la tête qui tourne sans perdre la tête)……”
—拉斐尔·昂多凡(Raphaël Enthoven),法国哲学家
“把我们归入奢侈品世界的想法并不一定适合我们。对我们来说,一瓶酒只有当它被喝掉时才算是真正地被出售了。我们主张分享、消费和当下的乐趣。我们没有欲望属于奢侈品世界”
—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Louis-Fabrice Latour)
法国勃艮第著名酒庄庄主

图片来源/Crédit Photo : Mathieu Garçon(马蒂厄·戛尔松)
作者|儒思忧|© 法兰西360
把一个颇受法国媒体青睐的年轻哲学家和一位具有两百年历史的勃艮第名酒庄的掌门人邀约在一起,边喝边聊,来一场“会话”,是不是一个好主意?这样一场“跨界”交流的结果又会是什么样?
2020年11月底,法国《星期天报》(Journal du Dimanche – JDD)照例出了一期和法国著名酒评媒体机构“贝丹+德梭(Bettane +Dessauve)”合作并由“贝丹+德梭”负责主编的名叫“Grand Art/大艺术”的葡萄酒、香槟与烈性酒增刊;
这期增刊的封面人物便是法国著名的年轻哲学家拉斐尔·昂多凡(Raphaël Enthoven),封面整版标题为“拉斐尔·昂多凡的酒与词(Le vin et les mots de Raphaël Enthoven)”,记述了哲学家与勃艮第名酒庄主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Louis-Fabrice Latour)的一次会面。
显然,这是一次试图在文学与葡萄酒酿制之间架设桥梁的会面。
按这场别开生面的对话记录整理者于莉雅·穆勒库(Julia Molkhou)说法,这是一次“必须紧急阅读(à lire d’urgence)”的高质量交流对话……
经征得该增刊版权拥有者“贝丹+德梭”的同意,法兰西360网站将这一“对话”用中文翻译与介绍如下,与热爱法国葡萄酒的朋友们分享。
图片来源/Crédit Photo : Mathieu Garçon(马蒂厄·戛尔松)
背景回顾:
地点:巴黎神话级(mythique)餐厅“Le Taillevent(勒达耶坊)”
这次哲学家和勃艮第名庄主的会面和品酒的地点在巴黎一家名叫“LeTaillevent(勒达耶坊)”的餐厅,位于巴黎第八区15 rue Lamennais。
据2021年1月18日发布的2021年版法国米其林星级餐厅指南,2021年,“Le Taillevent(勒达耶坊)”依然保留了它的星级地位,属于全法国74家两星餐厅之一(据最新数据,2021年全法国共有米其林星级餐厅638家,其中三星30家、两星74家和一星534家)。
说“依然保留”,那是因为这家餐厅的“米其林星运”曾几经周折,颇具传奇色彩。
这家以十四世纪厨艺大师、诺曼底公爵及法国查理五世(Charles V)和查理六世(Charles VI)国王御厨、法国历史上第一本法语食谱作者的别名命名的餐厅创办于1946年,1948年便获得了第一颗米其林星;1954年又获得一颗星;1973年便跻身于法国美食界精英中的精英俱乐部—米其林三星餐厅行列。
此后,“Le Taillevent(勒达耶坊)”的主厨多次易人;米其林“星”也曾先后两次被“摘”;第一次是2007年2月,当时的业主让—克罗德·维里纳(Jean-ClaudeVrinat)宣布在当年《米其林指南》中被摘一颗星,降为二星级;第二次是2019年1月,“Le Taillevent(勒达耶坊)”又被摘除一星。但2020年1月,米其林又恢复了它的两星等级;今年2021年,继续保持了两星地位。
自2020年以来,该餐厅的主厨是原来巴黎五星级酒店“Le Meurice(勒默里斯)”的主厨若斯林·艾尔朗(Jocelin Herland)。
“Le Taillevent(勒达耶坊)”餐厅是巴黎高级餐厅中最早打破波尔多酒专营制(exclusivité des vins de Bordeaux),把自己的酒窖对勃艮第和其它产区的酒开放的餐馆之一。
按照《米其林指南》评语的说法,该餐厅是一个具有“神话色彩的机构,是法式古典主义的巅峰(établissement mythique, sommum de classicisme à la française)”;
“指南”还特别赞扬餐厅“极其漂亮的酒单”,拥有3000多款不同的酒,每瓶价格自40欧元至16000欧元不等,可以满足各种层次顾客的消费需要。
自2011年以来,加尔迪尼埃(Gardinier)家族三兄弟成了“Le Taillevent(勒达耶坊)”餐厅的业主。加尔迪尼埃家族也是每年宣布法国龚古尔文学奖(Prix Goncourt)得主的巴黎“杜昂(Drouant)”餐厅以及波尔多圣爱斯岱夫(Saint-Estèphe)产区著名酒庄“飞龙世家(Château Phélan Ségur)”的业主。
另外,曾风靡全球、家喻户晓、并获得2007年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奖的美国动画片《料理鼠王》(Ratatouille)的背景设计就是受启于“Le Taillevent(勒达耶坊)”餐厅;为此,餐厅的名字也排列在《料理鼠王》片尾的鸣谢名单中。
图片来源/Crédit Photo : 来自网络
品尝的酒:科尔登(Corton)丘地两大名产区酒
—白葡萄酒:corton-charlemagne(科尔登—查理曼),2009年,大瓶装(magnum)
—红葡萄酒:corton-grancey(科尔登—格朗赛),2009年,大瓶装(magnum)
图片来源/Crédit Photo : 来自网络
人物简介:
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Louis-Fabrice Latour):
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是创建于1797年的勃艮第“Louis Latour(路易·拉图尔)”酒庄的现任庄主,是“拉图尔(Latour)”家族11代传人中的第七个“路易(Louis)”;
拉图尔家族拥有10公顷corton-charlemagne(科尔登—查理曼)、17公顷corton(科尔登),此外再加上它在Gevrey-Chambertin(热夫雷—香贝丹)、Vosne-Romanée(沃恩—罗曼尼)和Puligny-Montrachet(普里尼—蒙哈榭)的葡萄园,是勃艮第名庄中面积最大的酒庄,约有50公顷。
依照“贝丹+德梭(Bettane +Dessauve)”在一个专门介绍Louis Latour(路易·拉图尔)酒庄的视频中的说法,拉图尔是一个典型的有悠久家族传统的酒庄,可以说是现代Cordon(科尔登)葡萄酒,尤其是corton-charlemagne(科尔登—查理曼) 的发明者 ;
拉图尔家族最早从箍桶匠(tonnelier)起家—更有甚者,家族集团不仅直到今日还拥有一个年产3500个酒桶的酒桶制造厂,而且其注册地址还位于伯恩市“酒桶匠街18号(18 rue des Tonneliers)”;后来在购得葡萄园,成为酿酒人之后,在整个19世纪还一直以“酒商—箍桶匠(négociant-tonnelier)”著称,曾对伯恩济贫院(Hospices de Beaune)的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家族中的其中一位路易·拉图尔曾在很长时间内担任伯恩济贫院院长;也为勃艮第葡萄酒行业的发展作出过贡献,家族现任掌门人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自2003年以来担任勃艮第酒商公会主席(Syndicat des négociants de Bourgogne)。
拉图尔家族不仅擅长“多种经营”,而且在葡萄种植与酿酒发展方面具有不同寻常的战略发展长远眼光,不把自己禁锢于“勃艮第”这一地理区域,早在1979年,就已把触角伸到法国中南部Ardèche(阿尔岱什)地区,在那儿进行霞多丽(chardonnay)和维欧尼(viognier)葡萄品种的组合种植与酿造;1989年,拉图尔家族又把“战线”延伸至濒临地中海的法国Var(瓦尔)省,购得Valmoisine(瓦尔莫瓦西纳)酒庄,在那儿引入了黑皮诺(pinot noir)品种;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接手拉图尔集团之后,继续投资发展策略,于2003年在Chablis(夏布利)产区买下以一级和特级园以及气泡酒(crémant)著称的Simonnet-Febvre(西蒙尼–费尔夫)酒庄;五年之后(2008年),又在Beaujolais(博若莱)产区购入新品牌HenryFessy(亨利—费西)酒庄,使得拉图尔家族的葡萄酒产业布局达到鼎盛局面,不仅实现旗下酒庄产区风土品种多样化,而且也从适应气候及葡萄种植和葡萄酒产业未来演变的角度,作好了战略性的超前部署。
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本人生于1964年;在1999年24岁时继承家业,成为拉图尔家族第11代掌门人之前,他曾就读于巴黎Sciences PO政治学院,选择的是该校著名的培养法国政府高级行政官员的公共服务专业(Section Service public),毕业后曾在巴利巴(Paribas)银行工作过两年,并在英国伦敦实习数月。
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家族目前是法国500个最富家族之一;据法国《挑战/Challenge’s》杂志2020年法国500大财富排行榜,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和他的家族总排名第452位,法国酒庄庄主财富排名则居第43位;财富总值约1.8亿欧元;路易·拉图尔酒庄的酒出口至全世界120个国家。
图片来源/Crédit Photo : Mathieu Garçon(马蒂厄·戛尔松)
拉斐尔·昂多凡(Raphaël Enthoven)
拉斐尔·昂多凡1975年生于巴黎的一个犹太裔中产家庭,父亲让—保尔·昂多凡(Jean-Paul Enthoven)是一个作家兼出版商,母亲卡特琳娜·达维(Catherine David)是一位记者。
拉斐尔·昂多凡在巴黎蒙田高中(Lycée Montaigne)和亨利四世高中(Lycée Henri IV)毕业后考入巴黎高师,毕业后获得哲学学衔教师资格(Agrégé de philosophie),曾在里昂二大和巴黎七大(Jussieu)教过哲学课,但因在多家法国国营和私营电台电视台主持和制作哲学节目而著名;特别是2007年至2011年为“France Culture/法国文化电台”主持制作的“知识的新路(Les nouveaux chemins de la connaissance)”(该台现行另一著名节目“哲学之路/Les chemins de la philosophie”的前身)曾是法国文化台下载量最多、整个法国公共广播集团(Groupe Radio France)下载量第二的节目;
2011年至2012年,拉斐尔·昂多凡在欧洲第一广播电台(Europe 1)主持一个名为“拉斐尔·昂多凡眼中的世界(Le monde selon Raphaël Enthoven)”的每日晨间节目,从哲学角度阐释解读时事新闻所涉及的某些现象与概念,既有一定深度,又具有科普与趣味性,深得法国观众的喜爱,也使年轻哲学家声誉鹊起,影响力日渐增加;特别是2008年以来,拉斐尔·昂多凡每周在ARTE文化电视台主持一个哲学专栏节目,更加扩大了他的受众范围和声誉;
除了在法国广播电视媒体传播与普及哲学方面的成功之外,拉斐尔·昂多凡的个人生活也是充满“浪漫”与传奇色彩,也常常为某些追星族和媒体和所乐道。
他的前妻是法国著名哲学家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 Henri-Lévy)的女儿于丝蒂娜·列维(Justine Lévy),2000年,他“抢得”了他父亲当时的女友、后来成为法国前总统萨尔柯齐妻子的名模卡尔拉·布鲁尼(Carla Bruni),与其同居,并与于丝蒂娜·列维离婚。拉斐尔·昂多凡与卡尔拉·布鲁尼育有一子,名叫奥雷里安(Aurélien),生于2001年;2008年的某一天,法国人在电视里发现在埃及度假的时任总统萨尔柯齐肩上扛着一个8岁的小男孩,手牵他的新欢卡尔拉·布鲁尼;总统背的这孩子就是拉斐尔·昂多凡和卡尔拉·布鲁尼生的儿子……
他的这段非凡“情史”使他成为两位前妻/女伴作品中的人物:前妻丝蒂娜·列维在离婚后写了一本叫《什么都不重要》(Rien n’est grave)的小说,他成了书中人物亚德里安(Adrien)的原型;他后来的女伴卡尔拉·布鲁尼在息影T台之后曾“跨界”当歌星,自己写词作曲自己演唱,在2002年发行了第一张名为“有人跟我说(Quelqu’un m’a dit)”的歌集碟片,共有12首歌,其中第二首“Raphaël(拉斐尔)”唱的就是他。
2020年8月,拉斐尔·昂多凡发表了一部名为《赢得的时间》(Le temps gagné)的长达526页的“自传体”小说,如同一颗重磅炸弹,把巴黎“圣日耳曼德普莱(Saint-Germain-des-Prés)”和整个文化知识界炸得目瞪口呆:拉斐尔·昂多凡借助于原型清晰可辨的小说人物,对自己童年以来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人物,尤其是与母亲、养父、生父、哲学家BHL及其女儿、也即他的前妻于丝蒂娜和卡尔拉·布鲁尼等等的关系一一作了描述,除了对卡尔拉·布鲁尼流露一种眷恋之外,对所有其他人几乎都是“秋后算账”式的指责,引起极大反响,特别是他生父让–保尔·昂多凡对儿子如此明目张胆地外扬“家丑”感到痛心疾首,几乎要与儿子拉斐尔·昂多凡决裂,给当时疫情笼罩下抑郁消沉的圣日耳曼德普莱带来几分颇有古希腊悲剧色彩的气氛……
了解拉斐尔·昂多凡的这一“简历”对于理解这一“对话”也许有帮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最后提到的那一句……
图片来源/Crédit Photo : Mathieu Garçon(马蒂厄·戛尔松)
拉斐尔·昂多凡与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的“对话录”
于莉雅·穆勒库(Julia Molkhou):拉斐尔·昂多凡,您还能记得您喝的第一口葡萄酒吗?
拉斐尔·昂多凡:那时我七岁。那是一杯假装成水的白葡萄酒。我当时口渴得不得了,而葡萄酒又是那么的凉爽,等过了几秒种我才意识到喝的是酒。酒并不是我家最喜爱的东西,甚至都不是一个特别关注点。它是一种装饰。恰恰相反,我家对于风土喜好具有某种蔑视性的反应。这是一种圣日耳曼德普莱村民对脚踩泥土的人们的居高临下的审视。
我是通过阅读克莱芒·罗塞(Clément Rosset)的《现实:愚蠢论》(Le réel, Traité de l’idiotite)发现葡萄酒的。他用非凡的方式对酒醉(ivresse)进行了描写,并表明了酒醉是一种眼神的增加。
在克莱芒·罗塞看来,酒醉的人总要高于清醒的人一招。因为酒醉的人知道自己在胡说八道,而清醒的人则以为自己没有胡说八道。酒醉是一种意识到疯狂的疯狂,而事实上,世界被那些知道自己是疯子的疯子和那些以为自己是智者的疯子们所瓜分。
罗塞谈酒不同于任何人。真的是干货满满,足以让您改宗皈依。所以,我第一次接受了酒醉并不令人反感或并非一种残缺的想法;而是恰恰相反,酒醉是一种对某些人们平常所忽视的事物给予关注的方式。
这一切使我变得十分好奇,而且在这一好奇心之外,还加上我爷爷老是跟我说起他家里藏有几箱(阿尔及利亚)Tlemcen(特莱姆桑)坡地葡萄酒。这便是我是如何走入葡萄酒的。
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我们是有节制的人。比如,对我们来说,很难想象把勃艮第的酒和“酒醉”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爆炸性话题。
拉斐尔·昂多凡:很遗憾,因为酒醉是一个最美的话题。我们被道德过滤器剥夺了这一话题,而实际上这是一条通往人们并不总能得到的某些资讯的绝佳通道。全部赌注在于恰到好处地酒醉,让头晕转而不昏头(avoir la tête qui tourne sans perdre la tête)。
于莉雅·穆勒库:拉斐尔·昂多凡,您是不是在“醉得恰到好处”的状态下写您的第一部小说的?
拉斐尔·昂多凡:当门户打开,我只要把在我脑子里的东西誊写到纸上的时候,我就不再需要酒精、酒醉或精神药物(psychotropes);我只需要工作时间、香烟和安静。
于莉雅·穆勒库:在拉图尔家里,先从什么喝起?是不是有某种仪式?
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我是一家有两百年父子相传历史的企业的受托人。在勃艮第根基深厚,尤其在Corton(科尔登)。这是我们将在整个午餐过程中要品尝的酒。参观葡萄园,散步,这可以持续几年。我们可以从一种葡萄酒的历史入手。您知道,我们的担心是酒精依赖。所以得一步一步来。
图片来源/Crédit Photo : 来自网络
于莉雅·穆勒库:勃艮第是不是发生了很大变化?
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我八十年代读完巴黎政治学院回来的时候,那时的勃艮第可不是今天的勃艮第。而且那时我的同届同学们都不明白我要去那儿干什么。继承家业!在乡村生活!酿造葡萄酒!把自己封闭在这一行!今天可能对此会看好一些,但在当年,时髦的是波尔多产区的葡萄园。
从历史来看,勃艮第是一片红葡萄酒和黑皮诺的土地;近几年变白了许多,这倒是真的。变化是渐渐发生的。最早是葡萄根瘤蚜虫害(phylloxéra),它导致了不少霞多丽(Chardonnay)葡萄品种的重新种植。盎格鲁撒克逊人喜欢默尔索(meursault)、普里尼(puligny)或者夏莎涅(chassagne);我们丢失了红葡萄种植园,因为白葡萄酒更容易喝。
拉斐尔·昂多凡:默尔索(Meursault),这是卡缪(Camus)的《局外人》(L’Etranger)。我在想卡缪为什么给他取了这一名字?卡缪并不是一个很喜欢酒的人。但他很耐酒精。
这一点上萨特很敬重卡缪。因为萨特自己跟许多醉鬼一样很快就会喝醉酒(bourré)。卡缪则能挺住。他脑子里总想他父亲的一句话:“一个男子汉,得会自我克制(Un homme, ça s’empêche)”。
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默尔索(Meursault)是丘地产区唯一一个用村名为本地葡萄酒命名的村庄;而所有其它酒庄名都由产区名加村名组成,例如:Gevrey-Chambertin(热夫雷—香贝丹)、Pulugny-Montrachet(普里尼—蒙哈榭)、Vosne-Romanée(沃恩—罗曼尼)。
我喜欢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的一句话,它是这么说的:“在死前一定得喝默尔索,不然就会死得冤枉”。[译注:这儿有一个文字游戏:酒名“Meursault(默尔索)”与“meurt sot(死得蠢,死得傻)”的法语发音相同;这句话的法文原文是:“Il faut boire du meursault avant de mourir, sinon on meurt sot”]
于莉雅·穆勒库:1979年,路易·拉图尔家族在阿尔岱什(Ardèche)种了葡萄;1989年,又把葡萄种到了瓦尔(Var)省。今天还有哪些土地吸引您?
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您知道,勃艮第农用土地面积中,只有百分之一种了葡萄。空间还是有的。我们试图往奥克舒瓦(Auxois)方向发展,因为随着气候变暖,最好是往北部移动。如往南走,那就得选择海拔高的地方,以便能够利用夜间的凉爽,保证酸度。例如,在博若莱地区种黑皮诺(pinot noir)。我自己很喜欢博若莱(Beaujolais),这是一种很容易喝的酒。
拉斐尔·昂多凡:我没有日常喝的酒,因为我不每天喝酒。但我是在固定日期喝酒。比如,每个星期天,我准时在十二点前到“La Rotonde(圆顶屋)”,要一杯先哲酒庄的“Rochemorin”。这一习惯已足足持续了十年。
图片来源/Crédit Photo : Mathieu Garçon(马蒂厄·戛尔松)
于莉雅·穆勒库: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到底是什么东西使同行们对您如此信任?
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资历起很重要作用。在困难时期尤其看得清楚,人们依恋自己熟悉的名字和某种风格的酒。
于莉雅·穆勒库:贺拉斯曾说:“谁自信,谁就能引领他人”。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苦于自信太少?
拉斐尔·昂多凡:不。我们这时代在这一点上毫无特殊可言。不过,关于信心,有意思的是,认为信心是来自于外部的这一错觉;而事实上恰恰相反。是信心将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围绕信心的全部误会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相信必须有一个解决方案才能走出信心危机,而实际上是必须先走出信心危机,解决方案才可能呈现;
这一误会可以追溯到民主。信心是发端(inaugurale),是第一位的。在一个人们认为一切都糟糕的时代,人们总还是有一着,就是在桌上猛砸一拳,感受内心充满信心和喜悦的灵魂,就像米舍莱(Michelet)所说的那样。因为这是一项个人意旨,一项在某种意义上不被世界损坏的意旨。
这就是克莱芒·罗塞所说的卡门综合征(syndrome de Carmen)。卡门的故事骇人听闻,但音乐雄伟壮丽,战胜了我们。这便成为:生活是痛苦的,但是音乐的快乐战胜了生活的种种痛苦。这是人们可以对信心作的最好的定义。所以,信心完全不是21世纪的问题,这是所有人自古以来、并且也是永远的问题。
于莉雅·穆勒库:勃艮第情况还好吗?
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当然,餐馆在受苦,人们也在跟着它们受苦,因为勃艮第是餐饮业最具代表性的大区。酒窖业主(cavistes)生意不错,人们还是在那儿,我们忠实的客户继续在全世界追随着我们。葡萄酒有点像这不能再剥夺他们的最后一个乐趣。
我喜欢认为在一切都行的时候我们是一种奢侈品,而当情况不好的时候,就是一种消费品。我们非常自豪能够成为一种消费品。
我们在勃艮第都有农民血统。把我们归入奢侈品世界的想法并不一定适合我们。对我们来说,一瓶酒只有当它被喝掉时才算是真正地被出售了。我们主张分享、消费和当下的乐趣。我们没有欲望属于奢侈品世界。
拉斐尔·昂多凡:是的;但是您很难否认你们已身在其中,因为你们所出售的产品,无论它多么出色完美,都无法避免它绝对多余的特性。
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当然,不过它是一种有限的存在。而这就是消费。来,我们开一款大瓶装的corton-charlemagne(科尔登—查理曼),它的生命几分钟后即将完结。
我们非常在乎这一点。而相反,凡是说奢侈世界的,就是指贮存,搁在一边,收藏。
另外,第一次禁足的一个巨大惊讶是发现,与人们所能想象的相反,法国人喝的酒的质量没有下降。恰恰相反,被困在家里的人们喝的可是好酒。他们也还说读了不少名著。
图片来源/Crédit Photo : 来自网络
于莉雅·穆勒库:文化不也是一种一切都好的时候是奢侈品,一切都不行的时候是消费品吗?
拉斐尔·昂多凡:我也在想,普世意义上的文化,也就是说对他人和对世界的好奇心,是不是就来自于禁足。而小文化、寻找身份、想知道自己是谁的欲望、自己特有的传统或自己的小轶事却相反在一个一切都行的世界里得到恢复;就像好奇心随着禁足而增强,而无动于衷则也随着自由而蔓延。
于莉雅·穆勒库:你们呢,你们有没有利用禁足读一些不曾读过的东西,喝一些不曾喝过的酒?
拉斐尔·昂多凡:我利用禁足写了一部模仿(莫里哀)《太太学堂》(L’Ecole des femmes)的丑闻剧。
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啊,那您将被钉在示众柱上!
拉斐尔·昂多凡:当然,我不能悲叹我自己安排因由的事情的后果。但我把禁足用来工作了。我属于那些为数极少的充分地利用了这些在家度过的修道院式的时光。
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我在禁足期间也没读书。而且我很难把这段时间理想化,因为这是一种恐怖的紧张压力。一家葡萄酒批发行是一个企业。我们有几百号领薪雇员,他们停工了,但他们还是在,还需要鼓足他们的士气。
从人性角度看,这是一个极其难过的时期。我们曾为我们自己的存活、为不能付款的客户和为绝望的人们担忧。所以,我不会说我们干了照看婴儿的活,而是说我们承担了另一种我们毫无准备的角色。
于莉雅·穆勒库:你们是不是像建筑设计师卢狄·里希奥蒂(Rudy Ricciotti)那样害怕美的放逐?谈谈美和善?
拉斐尔·昂多凡:自19世纪以来,以波德莱尔(Baudelaire)为首,人们解释说,市民世界是美的杀手,人们把美标准化了,把美扼杀了。同一批人今天又说人们把美数码化了,融化在消费品中。
这是一种纠缠我们很久的担忧。任何时代都被看作是某一重要事物的黄昏。
卡缪说:“世界是美的,在它之外,别无救赎(Le monde est beau, hors de lui, point de salut)”。那么,假如美存在于一个目光或一个现象的相遇中,假如人们能够从一截玛德兰娜小蛋糕或者一口葡萄酒中萃取出美,那么我想美不需要任何担忧;
至于超越时间的美,例如建筑或绘画,它所受的考验既源于蔑视它的人们,也来自将它博物馆化和橱窗化的人们。想象一个人去梵高博物馆,买一本上面有梵高抽烟的骷髅头的日历。这样做的人,就是在玩把一件杰作变为产品的游戏,同时也得到了若不如此他无法见到的东西。我倾向于认为美再生的条件是恒久存在的。这是我的乐观主义。
图片来源/Crédit Photo : 来自网络
于莉雅·穆勒库:重读一本书是否能给予和重喝一种喜欢的酒一样的乐趣?
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在两种情况下,人们都希望重新体验一个曾经经历过的时刻。假如没有第一次惊奇,在一本没读过的书中或在一种不知道的年份酒中,在第二次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期待;其次,好酒是在演变的,这使我们每一次品尝的时候可以重新谈论它们。我们今天喝的corton-charlemagne(科尔登—查理曼)是2009年的,我知道它年轻时的味儿,我知道它充满阳光,几乎有点过于丰富;而今天我觉得酸性重新出现了。
拉斐尔·昂多凡:人们和喜欢读或重读的小说或散文保持着差不多的关系。人们常常指责书写文本总是对不同的问题作相同的回答。其实并不如此;因为一个文本与读它的人是不可分割的;我觉得如同味蕾培育一样,用眼光可以说出一本书是否变化了和是否变好了。
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比如《局外人》,您今天是否会以跟您年轻时接触它的不同的方式来阅读它?
拉斐尔·昂多凡:您可以把《局外人》当作一个本体论来阅读。世界是非人性的,世界存在那儿并不是要取悦于我,太阳把我烤焦,生活也并不顾忌我的喜好,但就是这样,这是荒唐的。我出生在那儿,我没有任何办法。人们也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叙事来阅读,一个对强加给他的痛苦无动于衷,甚至对他渴望的女人都感受不到爱的人的叙述。人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位杀死一个阿拉伯人都不觉得有何妨碍的殖民者的故事来读。人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决定向一具尸体连开四枪以确认他的自由的人对天空的宣战书来读。最后,人们还可以把它当作一种以上帝正义的名义对人的正义的批评,或者以人的正义的名义对上帝正义的批评来读。
同一文本让您滋生截然不同的感情。当人们在十六岁或十七岁时,会对《局外人》的白色写作非常震撼,觉得那小子冷漠无情;十年以后再读时,就会说:“啊,不管怎么样,他还阴茎勃起,他对她有欲望;他高兴,他忧伤,他发怒了!对于一个冷漠无情的人来说,这家伙倒还是有许多激情”。
作品随着读者自己演变。《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我就不跟您说了,这是一个恒常的万花筒。我想我们可以说一本书“陈酿变好了(il se bonifie)”,就像一款名酒一样。书卷因陈年而生色泽,受破损,页面也不再那么紧凑牢固了,但是语词却还是一模一样。这就是我对书的生命的辩护。
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您使用“bonifier(陈酿、变好)”一词;而这在佳酿世界里可是一个真正的话题。总有一个时候必须把酒喝掉;人们不可能无限等待。您看,这瓶charlemagne(查理曼)有十年了,是最完美的年龄。对一部作品是否也是这样?人们可以读一遍、两遍,但最后终于发现它老化了,不再适合我们?
拉斐尔·昂多凡:当然,这也有可能发生。人们可能停止喜欢。人们可以改变主意。改变趣味。在十八岁时需要读塞利纳(Céline)的散文,因为人们不高兴。然后,过了十年之后,又发现普鲁斯特(Proust)拥有意想不到的魅力,而在此前却一直把他看作一个能用四十页篇幅描写他如何入睡的病怏怏的同性恋者。这些书的类型随着性格的变化而演变。
于莉雅·穆勒库: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您对您的酒会改变意见吗?
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我们职业人士,比业余爱好者更会改变。我们感兴趣的,是曾经从一开始采摘葡萄的时候就在那儿,曾经做了某一决策,也许犯了一些错误;感到这些酒变化、成长。就像人们更关心一位从小就认识、并看着他长大和成为大人的儿童一样。
图片来源/Crédit Photo : 来自网络
于莉雅·穆勒库:对于拉图尔家族来说,承传与遗产是很重要的概念
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我们是祖传第十一代。我们是“Hénokiens(汉诺基人)”国际家族企业协会的成员,也就是说那些有两百年以上历史、始终属于创始家族,通常以家族名字命名并由家族管理的老字号企业群体。这一国际家族企业协会成立已经快四十年了,其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Beretta(伯莱塔)”(武器制造)公司。
我们勃艮第人不仅愿意谈过去,而且更喜欢谈未来。因为谈“Hénokiens(汉诺基人)”、谈滑铁卢大战后惠灵顿公爵订购拉图尔酒庄的葡萄酒,这固然很好;
但是,年轻一代、明天、气候变暖,对我们也很重要。
我们是现代人,不应该自我封闭在历史定格之中。而勃艮第人最惦念的事,首先是酿造好酒。遗产丰富了质量的标准,而质量与美和趣味一样在随着时间而演变。语词的选择也在变化。人们曾经喜欢谈论“压力/张力(tension)”,而今天则说“平衡(équilibre)”;
对我们来说,这种演变意味着用一家200多年的酒庄来吸引如今20岁至30岁的一代年轻人。
在这个意义上,我反对那种先入为主的想法,这一想法把勃艮第变成了一个葡萄酒既贵又不可触及的地区。“名窖(或名酒grands crus)”只占勃艮第产酒量的1%或2%;50%是价格在10欧元左右的大区级产区命名酒(appellations régionales),就像marsannay(马尔萨纳)或夏罗纳坡地酒(côte chalonnaise)这一类酒。
勃艮第在法国本国的形象并不是它在国外的形象。在迈阿密、纽约或旧金山,喝montagny(蒙塔尼)的,都是年轻人。这是一种时髦。
关于承传的想法,我们传给后代一个名字,Louis(路易),但更是一种葡萄酒的风格。一种不酒精过量的既细腻又强劲的酒。明天的敌人,是超过14度、甚至14.5度的酒。葡萄酒的乐趣则在13度。
拉斐尔·昂多凡:您知不知道,“A consommer avec modération(宜有节制饮用)”这一说法是出自塞纳克(Sénèque)的一句话?
对于斯多葛派禁欲主义来说,过度享受生存是生存享受不当;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伊比鸠鲁派相同;伊比鸠鲁享乐主义者通过控制他们的乐趣而试图使乐趣尽可能地持久延续。
节制是通往强度的道路。而过度则吞噬强度。传承也就是教会后来者享乐而不忍受。
阿波罗在成为太阳神和从建筑到音乐的所有人类学科的发明者之前,曾经是一个身怀暴力的神,暴力是如此之强以至他杀死了巨蟒蛇(Python)。为了赎罪,他在森林里度过了七年。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希望把节制的趣味传授给人们。他想教会他们限度(limite)。如果没有限度,就什么也没有。于是他就教他们城市规划、文学、建筑、音乐。所有为了存在而需要受限度和节律制约的一切。他是向人类表明没有节制就没有无限性可能的人,因为他自己经历了过度(démesure)。
图片来源/Crédit Photo : 来自网络
于莉雅·穆勒库:您希望跟谁一起喝一杯?
路易—法布里斯·拉图尔:我喜欢和其他专业人士一起喝酒。和他们可以重新体验历史。如果有机会和我们的竞争对手和朋友薇罗妮克·特鲁因(Véronique Drouhin)女士一起喝今天我们在这儿喝的这两款酒,那我会很高兴。我们可以在一起追忆那几年的葡萄采摘、我们各自所作的选择以及气象。
拉斐尔·昂多凡:可以有两类理想的对象。首先是小说中的英雄人物。
假如我能请来(小说《红与黑》中的)于连·索莱尔(Julien Sorel)一起喝一杯,那我就会对他说:“唉,跑去杀那小资太太,你脑子进水了!(Quand même, quelle idée d’aller tuer la bourgeoise)”;
或者和包法利夫人喝一杯,并对她说:“没那么严重,会好起来的;你欠债太多,很多人都碰到过这个。你情人走了,哎,这就是生活!”
然后,我倒是很想与国家元首们一起喝酒。作为人类文化研究者。我在这方面的经验很少。我了解最多的国家元首是尼古拉·萨尔柯齐(Nicolas Sarkozy),但他不喝酒。”
[感谢“贝丹+德梭”团队刘佳音女士为获得本文“对话”部分的中文翻译权而作的努力;也向“对话”法语原文记录整理作者于莉雅·穆勒库(Julia Molkhou)和图片摄影师马蒂厄·戛尔松(Mathieu Garçon)表示感谢]
资料来源/Sources
« Le vin et les mots de Raphaël Enthoven »
Le JDD – Grand Art : le supplément « Vins, champagnes & spiritueux » du Journal du Dimanche par Bettane+Dessauve, le 29 novembre 2020
“拉斐尔·昂多凡的酒与词”,刊载于2020年11月29日法国《星期天报》由“贝丹+德梭”编写的“大艺术”—葡萄酒、香槟与烈性酒增刊
其它资料出自/D’autres sources :
https://guide.michelin.com/fr/fr/ile-de-france/paris/restaurant/le-taillevent
以下为本站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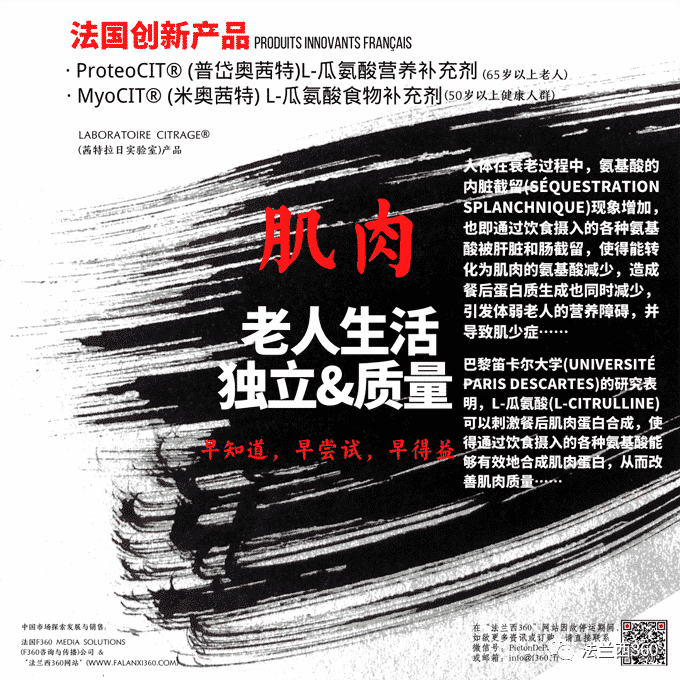
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申请书面授权请联系:
[email protected]
或微信号:
PietonDePar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