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小牧 丨《追忆似水年华》与维米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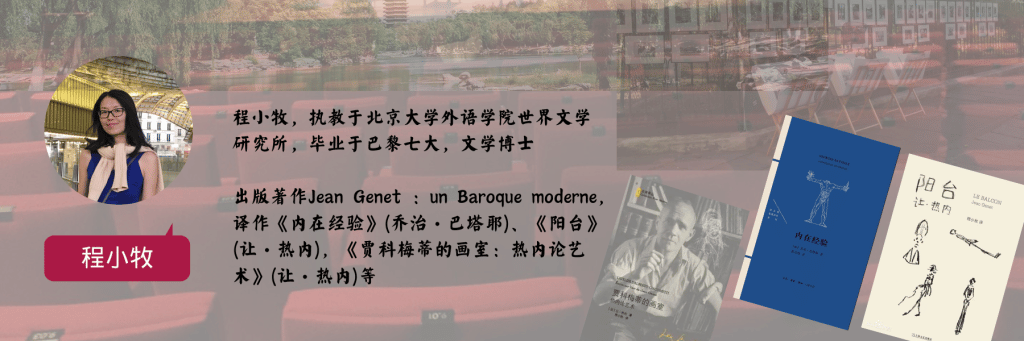

《追忆似水年华》与维米尔
文 / 程小牧
普鲁斯特(1871-1922)的《追忆似水年华》这部卷帙浩繁、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素以对各门类艺术的精微描写和独到阐释著称,其中涉及音乐、建筑、戏剧、摄影、家居装饰、古玩器物、服饰等,而绘画在整部作品中尤其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富于象征性的位置。

▲
马赛尔·普鲁斯特
约1895年
小说《追忆》详略不一地谈到一百多幅实存的古今画作,从14世纪早期文艺复兴至20世纪的未来主义,从乔托到莱昂·巴克斯(Léon Bakst);还有一些被粗略提及、难以对应于具体作品的绘画;更有许多虚构的画作夹杂其间,如小说中虚构人物、印象派画家埃尔斯蒂尔的创作。在《普鲁斯特的想象美术馆》(Le Musée imaginaire de Marcel Proust)一书中,埃里克·卡佩尔(Eric Karpeles)搜集到两百余幅与小说中的绘画或多或少相对应的油画、水粉水彩、版画及素描作品图录。
维米尔是所有这些画家中几乎被捧上圣坛的一位,在整部《追忆》中有着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维米尔在《追忆》中的反复出现,类似凡特伊的乐句,看似随意、零散、没有连贯的意义,好似一种来去无踪的神秘通感,但其实每次出场都是精心设计。最终叙述者以贝戈特之死的华丽篇章剥开了维米尔绘画的启示性内涵,普鲁斯特也终于道出维米尔在现实层面与自己紧密的精神联系。

▲
被认为是维米尔自画像的《老鸨》局部

维米尔在《追忆》中首次出现于《在斯万家那边》。奥黛特频频来访并向斯万发出约会邀请,斯万对她并无太多兴趣,便借口正在进行关于维米尔的研究而加以推托。其实斯万的这项研究,“已经中辍多年了”(卷一116)。
在《追忆》的写作年代(1906-1922),维米尔仍是一位鲜为人知、有待发掘的画家。素有“德尔夫特的斯芬克斯”之称的维米尔,一生从未出过这座小城,生前只在当地闻名,其生平也隐秘难考。从十七到十八世纪,他的名声限于收藏领域,未曾引起艺术史家的关注。维米尔被重新发现是在十九世纪,与一位法国人的努力分不开,此人即记者和艺术评论家托雷-伯格(Théophile Thoré-Bürger)。1866年,托雷-伯格在《美术报》(Gazette des beaux-arts)发表了一系列评论维米尔的文章,后结集出版,揭开了“发现维米尔”的序幕(A. Blum, Vermeer et Thoré-Bürger 13-14)。托雷-伯格对维米尔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出于自身的政治立场和价值理念,这位坚定的共和派人士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流亡北方。他厌恶被宗教、神话和历史题材所绑架的艺术史,一心要为风俗画(peinture de genre)正名。在当时的学院美术系统中,风俗画与静物画、风景画类似,在绘画体裁中的地位仍很低下,好似小品,不被看作严肃的创作。托雷-伯格却将专事表现市民阶层日常生活的维米尔视为真正的大师,维米尔之所以打动他,是因其“世俗与私密”(civile et intime)。托雷-伯格尽十数年之功潜心考据维米尔的画作,发掘原作、鉴别真伪,尤其是确定了一批无署名作品的归属。

▲
维米尔《写信的女士和她的女佣》
布面油画,约1871年,71.1 × 58.4 cm
现藏于爱尔兰国家美术馆
虽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普鲁斯特读过托雷-伯格的文章,但我们可以设想凭普鲁斯特对维米尔的热爱,应该对托雷-伯格有所了解。一个可能的间接证据是,普鲁斯特在《追忆》中坚持将维米尔名字分开写作两个音节“Ver Meer”,而在当时维米尔名字的通行写法已与今天一样,是合在一起的“Vermeer”。“Ver Meer”与托雷-伯格的写法一致。虽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一名字分开写另有深意,[1]但或许这一写法写只是在向托雷-伯格致敬。托雷-伯格对历史宗教等重大主题的厌倦和对维米尔绘画“世俗与私密”特质的颂扬,与普鲁斯特对艺术的思考高度一致。
普鲁斯特将上述种种思考赋予他的故事与人物。在《追忆》中,斯万出身资产阶级,却博文强识、不务俗事、风度超然、精通艺术且有着卓越的鉴赏力。斯万对维米尔的痴迷甚至到了要撰写一部关于维米尔的论著的程度,这是他的一大志愿,然而此事总是遥遥无期。确实,与奥黛特的恋爱消耗了斯万太多的精力,但从奥黛特来说,她是十分倾慕并支持研究维米尔这样的风雅之事的,这甚至是她和斯万之间罕有的“精神联系”:“她熟悉维米尔的名字如同熟悉她裁缝的名字一样。”(卷二34)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激情消亡的颓丧中,斯万也曾“恢复对维米尔的研究”,“想再到海牙、德累斯顿、布伦瑞克待一些日子”,考证一下“被当作尼古拉斯·马斯的作品的《狄安娜的梳妆》实际出自维米尔之手”(卷一351),然而这些研究计划一再搁置,最终被彻底放弃。
在《追忆》中,斯万与夏吕斯算得上最有文化修养的人。他们出色的才学使他们成为沙龙里的佼佼者,他们精微的品味与分寸,定义着无可模仿的高雅派头(chic),他们能够根据品味等级立即估量出某一人或一群体的阶层与水平。奥黛特追求派头,却根本缺乏这样的概念,其特征是她以为派头可以直接学会,不懂得这是由极少数人产生并在小圈子内扩展的品味;而斯万则对此无所不晓,甚至不必动用太多社交界的知识,仅看某次聚会有哪些人参加就能说出这个聚会是怎样的“派头”。“就跟文学家一样,只要你念出一个句子,马上就能确切地估测出作者的文学水准”(卷二242)。斯万喜欢交往作家和画家,并把他们介绍给叙述者小马塞尔,还将自己对乔托、波提切利、维米尔的兴趣传递给他,斯万是小马塞尔的文艺启蒙者。斯万对艺术的热情有一种近乎偶像崇拜(idolâtrie)的性质,他广博的知识在他的脑海中创造出艺术美的特定理念,他对现实的判断基于这样的参照,并虚幻地将之对应于现实个体。最初斯万对奥黛特的容貌并无太多好感,过于消瘦的脸颊并非他所好,只有在发现奥黛特的面孔酷似波提切利在西斯廷教堂的壁画《摩西的考验》中的“叶忒罗的女儿们”的少女肖像后,他才“把从美学观点出发所体会到的美运用到一个女人身上”,“他既然认识了《叶忒罗的女儿》有血有肉的原型,这种通感就变成一种欲望,从此填补了奥黛特的肉体以前从没有在他身上激起的欲望”(卷一 224)。同样,凡特伊奏鸣曲中的那个乐句,比奥黛特本人更激起斯万的深情,“奥黛特的感情中有所欠缺、令人失望的地方,那个乐句会来加以弥补,注入它那神秘的精髓”。从斯万在奥黛特陪伴下第一次在维尔迪兰夫人家听到演奏这个乐句感到目眩迷醉,到他无数次请求奥黛特为他弹奏同样的乐曲,这支曲子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爱情圣物。然而无论是奥黛特本人还是他们的爱情,并不会因艺术的加持而改变其真相,幻灭与厌恶随之而来。

▲
波提切利《摩西的考验》局部
壁画,1481-1482年,348 × 558 cm
现藏于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
小说中奥黛特的容貌酷似画中少女
这种对艺术的恋物癖式的沉迷、将现实物观念化的趣味,终究是将艺术看作美化日常的装饰。斯万并未真正理解艺术作品在他身上激起的感情,也不会试图解释他个人感觉的本质。尽管天赋过人,他却保留着肤浅的眼光,耽于莫名的快感,始终都是一个艺术爱好者。乐此不疲地将大量文学绘画作品作为可资占有和展现的知识或参照,有可能将年轻人引向错误的方向,甚至走向狭隘与浅薄。尽管斯万犹如精神父亲,但小马塞尔最终与他分道扬镳。在《重现的时光》中,马塞尔认识到,艺术的要旨在于对最寻常之物的重新发现,将被惯性和惰性遮蔽的最真切的现实转译出来,创作者负有一种使命,这需要坚定的意志并要求创作者为之牺牲。对艺术的偶像崇拜与对最真实之物的个人表达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斯万是无法与意志缺失作斗争的典型例子,其结果是他写作事业的失败——试图撰写关于维米尔的著作,但始终没有任何产出。正是斯万的失败让马塞尔领悟到在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之前必须犯的错误。斯万对他施加的影响非常强烈,直到叙述者马塞尔强大到足以将自己与他分离,否则他永远不会走向艺术创作,也永远不会找回失去的时间。斯万和叙述者马塞尔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并行关系,唯有通过否定、超越斯万,未来的作家才能踏上自己的写作之路。立志研究维米尔却一无所成,这一情节所指涉的内涵极为丰富。选中维米尔意味着斯万非同寻常的灵性与见地,也反衬着他的缺憾,同时维米尔本身作为隐喻符号也得以确立,也将他与叙述者马塞尔乃至普鲁斯特本人连接起来。

维米尔在小说中的另一种出现方式,是小说中的场景对维米尔作品画面的复现,好像将维米尔的画演成活动的一幕,令人想到沙龙里流行的“活画游戏”(Tableau vivant)[2]。勒内·于格(René Huyghe)曾强调过维米尔与普鲁斯特在目光上的“亲缘性”(Affinités électives),这种亲缘性使得两者的关联更为内在。当一些描写段落完全属于小说的叙述层,而不点名对维米尔的参照,某种程度上有赖于阅读者的认知经验去复现画面。这种方式看似隐蔽,实则是对维米尔绘画更为直接的指涉。
《在少女们身旁》中有一个奇特的段落,发生在马塞尔第一次乘坐火车前往巴尔贝克的旅途中。火车停在两山之间的一个小车站,马塞尔看到一位高大的姑娘背着一罐牛奶从车站小屋里走出来,向旅客出售牛奶咖啡。“晨光映红了她的面庞,她的脸比粉色的天空还要鲜艳”(卷二199),这位粗朴红润的姑娘“虽然与我一个人独处时头脑中描绘出的美貌模式毫无共同之处”,却让“我”突然重新意识到美与幸福,甚至“生活的欲望在我们心中再次萌生出来”。叙述者突然渴望被她看到,于是叫她,向她招手,她却没有注意到。“在她那高大的身躯之上,她的面庞是那样粉红、那样闪着金光,似乎别人是透过明亮的彩绘大玻璃窗在看她”,“她的面庞越来越宽阔,犹如可以固定在那里的一轮红日,我简直无法将目光从她的面庞上移开。这面庞似乎会向你接近,一直会走到你身边,任凭你贴近观看,那火红与金黄会使你头晕目眩”。当姑娘向他投过机敏的一瞥,为时已晚,火车已经开动了。

▲
维米尔《倒牛奶的女人》
布面油画,1660年,45.5 × 41 cm
现藏于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
这一段落,兀自独立存在,卖牛奶的姑娘灿烂的形象及其引发的强烈感情,脱离了上下文的背景与时间,也脱离了叙述时间,凝固成的一幅魅力无穷的画面,投向对过去和未来生活的沉思——“在这旅途的早晨,我生活的老习惯中断了”。我们无法不联想到维米尔的名作《倒牛奶的女人》(La Laitière),在这幅画中,一位同样高大健硕的年轻女子正在往罐子里倒牛奶。她身着黄衫蓝裙,立在一张摆满面包的桌子旁,光线从画布左上方的窗户射入照耀着她的脸,这是维米尔的室内女性肖像最经典的构图和用光。从这一点来看,小说文字特意写到姑娘好像被透过彩色玻璃窗的光照亮,也指向对维米尔画作的暗示。叙述者接下来又谈到属于某个地区的人的特殊的美感,这种美是这位卖牛奶的姑娘独有的,没有在这个地方生活过的人是无法模仿的;她的美是“土地的产物,人们从她身上可以品尝到土地独特的风韵”。这些思考也让我们想到维米尔作为荷兰画家的地域性特征,这位大师将北方生活风格的种种细节融入风俗画中,从建筑陈设、地砖窗格、装饰纹样到人物相貌,天才地捕捉到地域的独特性并将之提炼、展现于方寸之中。普鲁斯特在此表达了将这种感觉纳入小说的强烈愿望。
类似的画面复现也出现在贡布雷教堂的景象中。圣伊莱尔钟楼,是小镇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离多远都能看到。“钟楼细巧的塔尖,冒出在树梢之上;它呈淡红色,显得那么宜人(……)仿佛有谁故意在这尽是天然景物的图画的天空上,用指甲抠出一道艺术的记号”,“塔身石块上的暗红色调,尤其令人惊叹。在秋雾凄迷的早晨,看起来好像葡萄园暴风雨般的紫色之上升起一片绛红色的废墟,接近爬山虎的颜色。”(卷一65)在某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做完弥撒之后,眼前的钟楼“金光闪闪、焦黄诱人,简直像一块巨大的节日奶油包,带着鳞片及粘浆般的小滴阳光(égouttement gommeux de soleil)”。到黄昏时分,钟楼显得格外温柔,“它倚着天空,像靠在褐色的天鹅绒靠垫上似的,天空在它的压力下微微塌陷,仿佛为它腾出地方安息”。叙述者给教堂的钟楼涂上了丰富的颜色:粉红、绛红、紫色、金色和褐色。将塔楼比作带着鳞片滴淌粘浆的奶油包,显得非常奇特,如同将塔尖背后的天空比作凹陷的天鹅绒靠垫。

▲
维米尔《德尔夫特小景》
布面油画,1659-1660年,96.5 × 115.7 cm
现藏于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
今天我们已不太会把小说中贡布雷与它的现实原型伊利耶镇(Illiers)混为一谈,两者差别很大,贡布雷毕竟是一个虚构的地方。可以肯定,叙述者在这里为贡布雷的圣伊莱尔钟楼涂上的色彩与现实中伊利耶镇覆盖着石板的钟楼几乎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将小说中的描写与维米尔的《德尔夫特小景》相对照,我们会被色调的相似性所震撼:云影掠过的冷褐色,屋顶上的绛红色、蓝紫色,在天空云彩过度背景中的钟楼熠熠生辉的金色。如果仔细观察,《德尔夫特小景》最打动观者的是一种光学效果,对此维米尔的研究者们多有讨论并视之为维米尔的重要特征,这涉及一种绘画技法“光点法”(pointillisme lumineux),即用微小的白点的组合表现高光的闪亮和流动。勒内·于格形容这些亮点“如同深夜中灯火照亮的珠宝发出流动之光”(R. Huyghe, La Poétique de Vermeer 97)。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德尔夫特小景》的建筑物屋顶和立面的受光处布满这些亮点,尤其是金色的钟楼。仔细观看这些光粒子般的小点,或许我们会刹那间理解“鳞片”和“粘浆般的小滴阳光”的绝妙比喻。



▲
“光点法”
截取自《德尔夫特小景》
《倒牛奶的女人》《花边女工》
这些比喻应与普鲁斯特对维米尔的持久观察所留下的深刻视觉印象相关,普鲁斯特肯定曾被这些“光点”震撼过。《驳圣伯夫》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书的内容,我们写出的句子的内涵应该是非物质性的,不是取自现实中的任何东西,我们的句子本身,一些情节,都应以我们最佳时刻的澄明通透的材料构成,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处于现实与现时之外。一本书的风格和寓言就是以凝结的光的滴状物(gouttes de lumière cimentées)形成的。”或许这句话可以被看作对维米尔的第一次暗示。
这里“凝结的光的滴状物”与“粘浆般的小滴阳光”的说法确实惊人得相似。普鲁斯特对维米尔的画面复现,绝非仅是从画面到文字的挪用转化,这其中包含着观察世界的目光与创作技法的隐喻。这是他们之间真正的“亲缘性”所在。普鲁斯特最看重的维米尔作品就是《德尔夫特小景》,这并非偶然,因为这幅画最大程度地体现了这种亲缘性。我们将在小说人物贝戈特之死的段落中,读到这幅画的辉煌启示。

贝戈特在观看维米尔的《德尔夫特小景》时,因杰作所激起的炽热感情和痛苦思考而病痛发作,以至于猝死于画前。这是《追忆》中极不寻常的一个段落,可能是最为“浪漫”的一个段落——在通俗小说“罗曼司”的意义上,浪漫一词并非褒义,特别是对于《追忆》这部第一人称的现代作品,《追忆》是以其严苛地表现日常真实而著称的。虽然从“似真性”来说,这一情节勉强可信——贝戈特长期罹患尿毒症,而同样的疾病已夺走了叙述者祖母的生命,但如此突兀的情节在整个叙事中仍显得夸张。
虽然贝戈特这位小说所虚构的作家,曾是少年马塞尔的楷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失去了权威,他长期患病的身体也使他变成一个令人怜悯的老人。去世那天,他本应休息,但由于巴黎正举行一次荷兰画展,“一位批评家在文章里谈到维米尔的《德尔夫特小景》中一小块黄色的墙面画得极其美妙,单独把它抽出来看,就好像是一件珍贵的中国艺术品,具有一种自身的美”(卷五180),于是十分喜爱且自以为很熟悉这幅画的贝戈特,决定前往美术馆看看原作。在维米尔的画前,贝戈特目眩神迷:“他头晕得更加厉害,目不转睛地紧盯住这一小块珍贵的黄色墙面,犹如小孩盯住他想捉住的一只黄蝴蝶看。‘我也该这样写,’他说,‘我最后几本书太枯燥了,应该涂上几层色彩,好让我的句子本身变得珍贵,就像这一小块黄色的墙面。’这时,严重的晕眩并没有过去。在天国的磅秤上一端的秤盘盛着他自己的一生,另一端则装着被如此优美地画成黄色的一小块墙面。他感到自己不小心把前一个天平托盘误认为后一个了。”(卷五180)
贝戈特不断喃喃自语“带挡雨檐的一小块黄色墙面,一小块黄色墙面”,而后跌坐在一张环形沙发上,不久便因病痛发作倒地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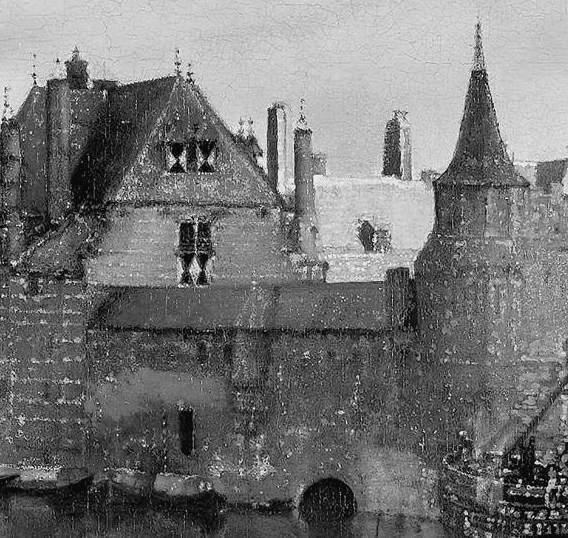
▲
《德尔夫特小景》局部:“一小块黄色墙面”
如把对比度调大或将图片调成黑白
可以看出这块墙面十分明亮
首先要指出的是,这一段落强烈的自传性,普鲁斯特的书信及相关研究已经完全印证了这一点。小说中所描写的画展,是1921年春天在巴黎老式网球美术馆举办的荷兰绘画展,其中有三张维米尔的作品:《德尔夫特小景》《倒牛奶的女人》和《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这位对当时公众来说仍很神秘的荷兰大师传世作品极少,其代表作在巴黎的展出,引起了文艺界的高度关注。与普鲁斯特相识的评论家沃杜耶(Jean Louis Vaudoyer)在《见解》周刊(L’Opinion)连续发表三篇文章,阐发了一些独到的观点,其中就提到了“一小块黄色墙面”。对维米尔长期抱有隐秘热情的普鲁斯特看到文章后相当激动,立即给沃杜耶写信祝贺他,并向他吐露自己的感受:“自从我在海牙美术馆看到《德尔夫特小景》之后,我知道我见过了世界上最美的画”(Correspondance, t.4 86)几天后,他又写到,“您知道维米尔是我二十岁以后最喜爱的画家,这一偏爱有诸多迹象,其中之一就是在1912年的《在斯万家那边》中,我让斯万去写一部维米尔的传记”。

▲
维米尔《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布面油画,1665年,44.5 × 39 cm
现藏于毛里茨之家博物馆
普鲁斯特似乎有意识地将自己对维米尔的喜好尽量前推,他二十岁时应是1890年左右,如果当时就已发现维米尔确实令人惊叹,因为这位画家直至十九世纪都只为极少数精英所知。不过实事似乎是1902年10月与费奈隆同游荷兰时,普鲁斯特才通过《德尔夫特小景》而了解维米尔(Lettre retrouvé 58)。1921年,沃杜耶的展评文章促使普鲁斯特下决心去巴黎的展览上重温《德尔夫特小景》,他在信中问沃杜耶:“您是否愿意带我这样一个垂死的人去看展览,让我倚在您的胳膊上?”(Correspondance, t.4 129)沃杜耶欣然应允。此时距普鲁斯特去世仅剩一年半的时间,他的身体已极为虚弱,几乎已不再出门,而修改和发表《追忆》的繁重工作也让他倍感与时间赛跑的疲惫。贝戈特在《德尔夫特小景》前感到致命的晕眩并被死亡击中,这最后增添上去的段落之一,或许并非完全虚构。1923年,沃杜耶在写给友人的信里回忆道:“他(普鲁斯特)满怀仁慈和宽容的友情阅读了我给《见解》周刊写的普鲁斯特评论。我所提到的‘小块黄色墙面’的段落击中了他(……)那天上午,在老式网球美术馆,普鲁斯特身体极为不适(……)好几次,他退回来坐在那个环形沙发上,而贝戈特将从那个沙发上倒地死去。”(J-V. Tadié, Proust : Biographie 873)



▲
始建于1861年拿破仑三世时代的老式网球场
位于巴黎杜乐丽公园西侧,于1909年改建为美术馆。普鲁斯特1921年所看的维米尔画展就是在这里举办的。该场馆现为国家美术馆,主要展示现当代影像艺术作品。
沃杜耶的见证令我们惊讶地发现,贝戈特之死与普鲁斯特本人的经验高度重合。实事上,与维米尔发生重大关联的两个小说人物斯万和贝戈特,不仅在文本层面与叙述者有着紧密的对应,在现实层面与小说作者本人也有着内在的契合,而无论在文本层面还是现实层面,将他们联系起来的都是维米尔。斯万作为叙述者的精神之父,以自身的失败——写一部关于维米尔的书而终未完成——而将叙述者推向作家之路,这是叙述者唯一与自己相比较的人物;而小说中贝戈特与叙述者有着同样的职业——作家,他们都从维米尔的画作中得到了创作法的启发。在现实层面,普鲁斯特的荷兰之行和巴黎观展中对维米尔的思考,直接融入了他对斯万和贝戈特这两个人物生平与事业的构思。
在贝戈特之死中,有关维米尔的主题在小说中再度回归和升华,并与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家的天职等重大问题联系起来。作者跳出了小说的叙述层,直接叩问维米尔所带来的启示究竟何在。

对于普鲁斯特来说,一件艺术作品,无论一幅画还是一本书,都是一个视野问题。他将艺术家比作一位给病人矫正视力的眼科医生:“一个独辟蹊径的画家,一个独树一帜的艺术家,要想受到公认,必须采用眼科医生的治疗方法。用他们的画或小说进行治疗不总是令人愉快的。治疗结束后,医生对我们说:现在请看吧。我们看见的世界(不是被创造一次,而是经常被创造,就像一个独出心裁的艺术家经常突然降世一样)同旧世界大相径庭,但一清二楚。”(卷三322)就像一个近视者戴上眼镜而重振视力一样,画布揭示了隐藏的方面,让观众体验到一个直到那时他还未知的世界。在《重现的时光》中,马塞尔提出了这样一种思考:“作品只是作家为读者提供的一种光学仪器,使读者得以识别没有这部作品便可能无法认清的自身上的那些东西。”(卷七217)如果考虑到维米尔所使用的“暗箱”技术,我们会再次惊诧于普鲁斯特与维米尔的亲缘性。自从大卫·霍克尼提出这一假设以来,很多研究者都证明了维米尔借助暗箱这一光学设备作画的事实,以获得肉眼无法达到的形的准确和高光扩散的独特效果,因为“暗箱会缩小物体的比例,但不会减少物体反射的色彩或光量,所以颜色的强调和光的对比看起来比在自然视觉中更加强烈”(A.K.Wheelock, Jan Vermeer 96)。

▲
维米尔《地理学家》
布面油画,1668年,53 × 46.6 cm
现藏于德国施泰德艺术馆
我们无法确定普鲁斯特在欣赏《德尔夫特小景》时是否知道维米尔曾使用这种光学设备,但普鲁斯特将艺术家比作眼科医生,通过矫正一种视野而成为新世界的创造者,这与维米尔所实践的创作法是不谋而合的。维米尔之所以令贝戈特如此震惊,是因为他揭示了贝戈特无法用肉眼看到的隐藏的真相,它集中体现在那“一小块黄色的墙面”上,既包含着认识,也包含着方法。如同迪迪-于贝尔曼所指出的,“黄色”这个形容词,究竟是形容“墙”,还是形容“面”呢,或者说,让贝戈特得到终极启示的究竟是“墙”还是“面”呢?如果“黄色”是形容“墙”,则关乎对事物的再现;如果是形容“面”,则关于形式的创造,“面”具有独立的价值(迪迪-于贝尔曼《在图像面前》352-353)。
维米尔籍籍无闻的一生与伟大的传世之作之间的对比对普鲁斯特而言构成了某种终极启示。在贝戈特死去的那一刻,叙述者马塞尔也终于懂得,对于艺术家来说,一切此生的幸福都是虚浮假象,唯有作品才有价值,才能超越时间与肉身。《追忆》的写作始于生活的终结,它站在死者的一边,将全部逝去的人生凝结为一部唯一的书。艺术家的天职就是做艺术的仆人,为作品而劳作,他背负着常人不可能理解的沉重义务。普鲁斯特在感叹自己变成这不幸被选中者的一员时,再次看到了维米尔的身影:
人们只能说,今生今世发生的一切就仿佛我们带着前世承诺的沉重义务进入今世似的。在我们现世的生活条件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以为我们有必要行善、体贴、甚至礼貌,不信神的艺术家也没有任何理由以为自己有必要把一个片断重画上二十遍,他由此引起的赞叹对他那被蛆虫啃咬的身体来说无关紧要,正如一个永远不为人知,仅仅以维米尔的名字出现的艺术家运用许多技巧和经过反复推敲才画出来的黄色墙面那样。所有这些在现世生活中没有得到认可的义务似乎属于一个不同的,建立在仁慈、专注、奉献之上的世界。”(卷七 181)
本文原发于《外国文学》2021年第6期,原文标题为《中维米尔的三重出现及绘画的隐喻》,刊发于“山水澄明”时作者有修订与改动。
注释:
[1] 菲利普·布瓦耶认为“Ver Meer”与“vers mère”(朝向母亲)谐音,而“Delft”(德尔夫特)与“Delphes”(德尔斐神殿)谐音,于是“Ver Meer de Delft”(德尔夫特的维米尔)就有了“Vers mère de Delphes”(朝向德尔斐神殿的母亲)之意。寓意维米尔的艺术如同母体,在艺术圣殿上传达着神谕。(P. Boyer, Le Petit pan de mur jaune 94)
[2] 指参照一幅名画的构图,人们扮成画中人,穿上相同的服饰,配上同样的布景,将画面演出来。曾是沙龙中流行的娱乐,一种现实模仿画面的反向游戏。
以下为本站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