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映虹|尤瑟纳尔及其《苦炼》
[转载注] 本文为北京大学法语系段映虹教授的一次讲座回顾,由北大法语系研究生孟瑶整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微信公众号原创首发;本站经段映虹教授及北大“比较所”授权转载。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2022年6月8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生专业选修课“法国文学选读”的最后一次课上,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段映虹教授应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高冀老师的邀请,做线上随堂讲座,讲解尤瑟纳尔及其代表作《苦炼》,并与选课同学互动交流。本次讲座采用腾讯会议网络研讨会模式,将选课同学设为嘉宾,同时向观众开放。全国各地数百位师生线上旁听,反响热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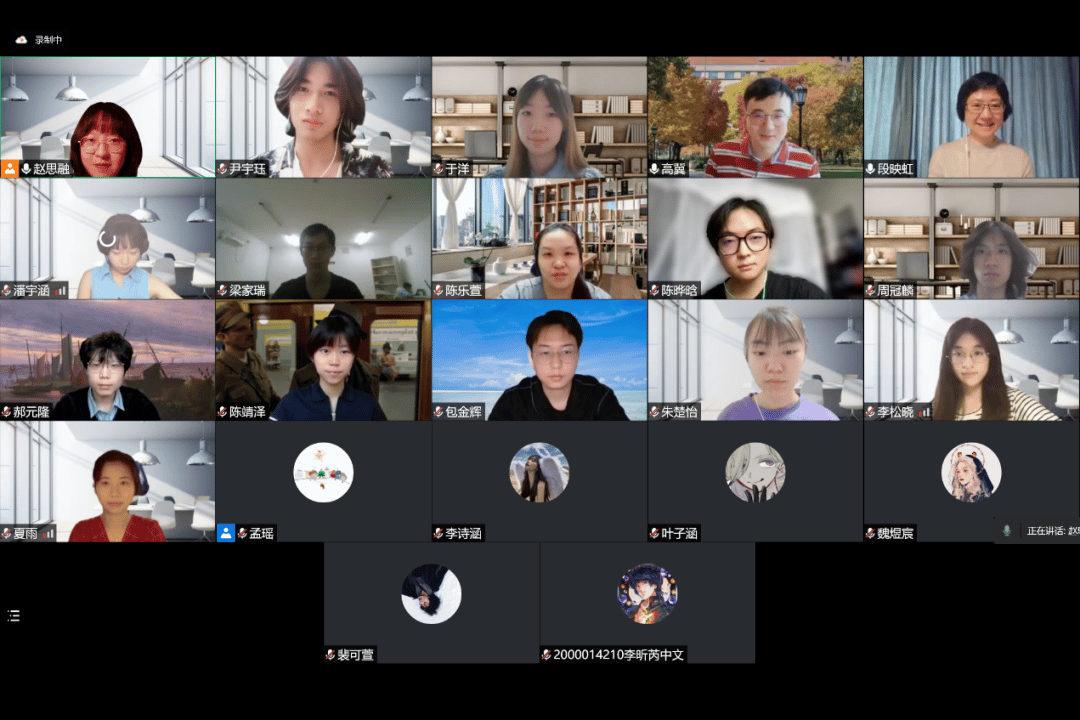
线上讲座现场
【本篇讲座纪要由北大法语系研究生孟瑶整理。在此感谢!】
主讲人介绍
作为“法国文学选读”这门课程的任课教师和本次讲座的主持人,高冀老师强调,《苦炼》有着丰富的意涵,以泽农这一兼具炼金术士、医生和哲学家三重身份的虚构人物为线索,描绘出一个丰满立体的文艺复兴时代。与此同时,小说内容涉猎广泛,勾连起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的大量历史文化背景,其中涉及的诸多内容,如宗教改革、印刷术的诞生及其影响等,都与《法国文学选读》课程此前所讲的内容构成对话关系。高冀老师也谈到,主讲人段映虹教授是尤瑟纳尔研究专家,曾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翻译《苦炼》,让中国读者得以在母语语境中领略这部杰作的风采,而这次讲座的机会十分难得,希望能让更多的读者关注尤瑟纳尔及其作品。
在进入正题之前,段映虹教授提醒大家注意讲座日期选择的巧合——6月8日正是尤瑟纳尔的诞辰。虽然尤瑟纳尔不懂中文,但她热爱中国古典文学,通晓中国古典哲学。如果她在天有灵,知道我们使用她所热爱的老子、庄子、李白、杜甫的语言介绍她的作品,定会非常开心。
尤瑟纳尔在1903年6月8日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1987年12月17日在美国缅因州的荒山岛上去世。她出生和去世都不在法国,作品极少以法国为背景,主人公也极少是法国人。尽管如此,尤瑟纳尔仍是20世纪最伟大的法国作家之一。在《哈德良回忆录》(Mémoires d’Hadrien)中,尤瑟纳尔曾借哈德良之口说:“我用拉丁语治理国家……但是我用希腊语思考和生活。”尤瑟纳尔也是如此,出生和去世的地方也许只是偶然,但她用法语来思考和生活,其典雅优美、精准洗练的语言是法语的荣光。与大部分法国作家不同,尤瑟纳尔摒弃了法国中心主义甚至欧洲中心主义,其作品以广阔的视野展现了极其多元的时空背景。
尤瑟纳尔的生平有两个独特之处。首先,虽然尤瑟纳尔的作品以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哲思见长,但她本人从未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她从小热爱阅读,并跟随父亲游历欧洲各地,阅读和旅行才是她真正的“学校”。其次,作家本有一个古老的家族姓氏(de Crayencour)。她在18岁发表第一部作品时,与父亲通过文字游戏,将原有姓氏的字母打乱,重新拼成新的姓氏(Yourcenar)。自此,尤瑟纳尔便成为作家的笔名,后来在1947年正式成为其合法姓氏。
接下来,段映虹教授从作家手记、《苦炼》原文中选取重要文段,细致梳理了小说的创作背景和重要意涵。
“作家的相当一部分作品,将在半个多世纪里经历一系列无法预料的变迁之后,出自十九岁到二十岁之间这些纷乱的梦想里。”正如尤瑟纳尔所言,年轻时代这些纷乱的梦想里,孕育着后来《苦炼》和《哈德良回忆录》等作品的萌芽。其后,尤瑟纳尔时写时辍,直到1956年才真正开始重写《苦炼》,花费十多年时间,终于在1968年出版。此时的尤瑟纳尔已经六十五岁了。因此,在《苦炼》的创作笔记中,尤瑟纳尔写道:“开始写作《苦炼》(以另一个名字为题)时,我跟小说开头年轻的泽农和年轻的亨利-马克西米利安一般年纪。作品完成时,我比泽农和亨利-马克西米利安撞上他们的死亡时年纪稍长。”这便是《苦炼》漫长的成书过程。
段映虹教授坦言,将小说的题目(L’ Œuvre au Noir)译为“苦炼”,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该书名取自欧洲中世纪炼金术术语,字面意义为“黑功”,指代以炼成点金石为目的的“大功”(le Grand Œuvre)的第一个阶段,即在坩埚中对物质进行煅烧、融解和分离,使物质达到“腐化”状态,以提炼出纯粹成分的过程,这是实现“大功”的过程中最艰辛、最危险的步骤。其后的“白功”(l’Œuvre au blanc)是对前一阶段提炼出的物质进行清洗和进化,而最后的“红功”(l’Œuvre au rouge)指的是熔炉内的物质即将转化为点金石之前的炽热状态,也象征着炼金术士因获得对物质和自身的深入认识而达到的身心陶醉状态。小说的主人公泽农不满足于接受任何现成的概念,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用毕生的观察、实践和思考来努力获取接近于真理的知识。尤瑟纳尔正是用“黑功”来象征泽农一生的求索,理解这一隐喻对把握小说的含义至关重要。
在进入具体的分析之前,段映虹教授也对小说的历史背景做了简单说明。泽农1510年出生在比利时布鲁日,那里是当时欧洲最重要的羊毛集散地和金融中心之一。泽农是一个富商家庭的私生子,从未见过他的父亲。他二十岁时决定离家出走,到大千世界去探寻知识,在外游历三十多年后隐姓埋名,重回故乡。最后,因为一个意外事件,泽农暴露了真实身份,被判火刑,在1569年2月去世。《苦炼》法文版口袋本的封面选取尼德兰画家勃鲁盖尔的画作《雪中猎人》,非常恰切。勃鲁盖尔几乎是泽农的同时代人,只比泽农晚几年出生,又与泽农同一年去世。这幅画作于1565年,差不多是泽农回到布鲁日定居的时期。画中呈现的冬日场景也是泽农在冬天所见的场景。画中的冬天虽然严酷却充满生机,是那个时代的诗意写照。

《苦炼》法文版口袋本封面,伽利玛出版社1981年版
还需注意的是,泽农一生游历过世界上很多地方,经历过很多历史事件,而尤瑟纳尔的写作深入到历史的肌理,从那个时代人们的视角出发,描述当时发生的事件。首先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泽农曾在土耳其宫廷供职,这将成为他后来被审判时的罪状。从1517年路德在维滕贝格发表关于赎罪券功效的《九十五条论纲》,到1564年加尔文在日内瓦去世,泽农生活的时代也恰好与宗教改革的进程并行。这其中既有天主教与新教的对立,也有新教内部各派别间的纷争,泽农的母亲希尔宗德经历的明斯特之围便是一例。此外,还有与宗教对立密切关联的政治冲突,即西班牙与法国对欧洲主导权的争夺,这正对应了小说开头亨利掷硬币选择为查理五世或弗朗索瓦一世效力的情节。在西班牙与法国的竞争中,意大利和佛兰德斯正是主战场,这两个地方也正是小说着重描写的地点。在更远的地方,新大陆的发现冲击了旧世界的秩序,引发对世界的重新分割以及金融资本实力的上升……它们的广度和影响难以为当时的人们所窥见,但都构成泽农一生的广阔背景。
接下来,段映虹教授从《苦炼》第一部《漫游岁月》的卷首语切入,对小说文本进行细读。
“哦,亚当,我没有赋予你属于你自己的面孔和位置,也没有赋予你任何特别的天赋,以便由你自己去期望、获取和拥有你的面孔、你的位置和你的天赋。自然将另一些类别禁闭在由我订立的法令之内。然而,你不受任何界线的限制,我将你置于你自己的意志之手,你用它来确定自己。我将你置于世界的中央,以便让你更好地静观世间万物。我塑造的你既不属于天界,也不属于凡间,既非必死,也非永生,以便让你自己像一个好画家或者灵巧的雕塑家那样,自由地完成自己的形体。”
这段话摘自意大利人文学者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的《论人的尊严》,为主人公的漫游岁月奠定了基调。在皮科看来,人在“存在之链”中没有明确的位置。世界上其他物种(动物、植物、矿物)都只能被动承受外部力量的作用,而人可以通过学习、思考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来提升自己在“存在之链”中的位置。上帝创造亚当,没有对他做出任何限制,而是让他凭借自由意志塑造自我。在文艺复兴早期的人文主义者看来,这便是人的自由所在,也是人的尊严所在。
小说开篇讲述泽农离开布鲁日,与表弟亨利-马克西米利安在大路上相遇。作为权贵之家的私生子,泽农很难继承财产,最好的出路便是成为教士。但泽农对于这样被规定好的人生之路毫无兴趣,因此在二十岁时离开家庭,外出寻求知识。而亨利-马克西米利安虽为欧洲最富有的家族之一的合法继承人,却也不愿接受被规定的命运,因而也选择离家出走,追求自我的实现。他们在大路上相遇,亨利满怀豪情宣称自己将要建立与亚历山大和凯撒齐名的功业,“要紧的是成为一个人”。泽农鄙夷俗世的虚荣,不无傲慢地回答:“对我来说,要紧的是不仅仅成为一个人。”至于何为“不仅仅成为一个人”,则关系到泽农一生的求索。泽农接着说:“如果一个人在死去之前连自己的牢狱都没有走上一圈,岂不荒唐?”这句话对我们理解小说、理解尤瑟纳尔,对指引年轻人的生活都有重要意义。泽农借用“牢狱”来比喻一个自由的人可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意指人应当尽量抵达自己能力所至的极限。虽然在泽农的时代,人们的活动范围相比如今要小很多,泽农却尽力扩大行走的边界。他到过北极圈,也去过中东、近东、北非等地,不断扩展自己的认知范围,但他最深刻的蜕变却是在布鲁日的一个小房间里完成的。尤瑟纳尔本人也热衷旅行,她认为旅行不仅能增长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能促进对人自身的思考和完善。泽农所用的比喻,日后将成为尤瑟纳尔记述自己一生中最后游历的著作的名称,《牢狱环游》(Le Tour de la prison)。

《牢狱环游》法文版封面,伽利玛出版社2013年版
由此可见,对于尤瑟纳尔而言,泽农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而是如同一个真实的人一般存在。尤瑟纳尔曾说,如果一个创造的人物不像一个活着的人那样真实和对我们重要,他就毫无意义。表兄弟两人分手时,亨利问泽农为何步履匆匆,泽农答道:“另一个人在别处等着我,我正朝他走去。”面对亨利的疑惑,泽农补充道,那个人就是“泽农在此。我自己”。需要强调的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基本是一个由南向北推进的过程,泽农年轻时代的16世纪早期,佛兰德斯地区的文艺复兴才刚刚开始。泽农这些充满青春的热情与骄傲的话语,与15世纪意大利的皮科的卷首语相呼应,宣示了文艺复兴早期人文主义者对人具有无限潜能、对人的自我完善抱有的坚定信念。接下来是三十余年的漫游岁月。泽农去过莱昂的修道院,跟随有卡巴拉倾向的炼金术士学习,也在大学里学习过医学。他的足迹遍布欧洲各国,曾在黑死病疫区救治病人,行踪远至阿拉伯、北非和北极地区。他写过几部医学和哲学著作,其中包含一些令教会不安的言论,数次面临教廷的缉捕。
《漫游岁月》以泽农和亨利二人的相遇开始,小说第一部的尾声也讲述了亨利的死亡:
“他常常设想自己死去的方式和情形:他可能被一颗火枪子弹击中,鲜血淋漓,高贵地躺在西班牙长矛华丽的残骸上,王公们为他叹息,战友们为他哭泣,最后覆盖着一段动人的拉丁文铭文,葬在教堂的墙根下;……在间日虐期间敲响的阵阵钟声里,他以为听见了凄厉的短笛和嘹亮的长号,向世界宣布一位君王辞世的消息;他感到吞噬这位英雄并将他带往天上的火焰在自己的身体里燃烧。这样的死亡,这些想象中的葬礼才是他真实的死亡,是他真正的葬礼。……他的外套口袋里有他的《女性躯体颂》手稿;他曾期待这些活泼温柔的小诗为他带来一点名声,或者至少在美人们面前获得一点成功,然而这本诗集的命运终结在坟坑里,跟他一起葬在几锹黄土之下。他为了向皮科洛米尼夫人表示敬意而费力刻下的一句铭文,长久地留在丰特布兰达的井栏上。”
亨利曾无数次想象自己的死亡,而当死亡真正来临时,他从马上摔下,只是感到一阵震颤,甚至没来得及感受死亡。他向往的功名、财富、爱情,以及诗人的声名,都没能实现。但是正如泽农之后在深渊里回忆自己一生的经历时所想的那样,一切都跟我们当初预想的不一样,但又并非完全不一样。
如果说《苦炼》的第一部囊括长达35年的时间跨度,第二部《静止不动的生活》,则是描写泽农回到布鲁日后几年的定居生活。泽农原本以为故乡只是漂泊路上的一站,然而种种始料未及的情况让他滞留下来,正如尤瑟纳尔1939年离开法国前往美国探望朋友时,并未想到她在多年后才重返欧洲。战争的爆发使她原本只有几个月的旅行延长至12年的定居。由此可见,作品的构思会因作家个人的经历而变得更加丰富。
“就在不久前,他重新走在布鲁日蜿蜒曲折的小街巷里时,他还以为经过三十五年动荡不安的生活之后,离开追求抱负和知识的大道,这个歇脚处会让他得到些许休憩。他以为自己会体会到一种令人担忧的安全感,就像一只动物为自己选择一处栖身之地,只因那里的狭小和幽暗让它安心。他弄错了。这种静止不动的生活在原地沸腾;他感到一种几乎令人害怕的活跃像地下河一样涌动。”
恰恰是在布鲁日这个狭小的地方,泽农经历了最彻底和最剧烈的蜕变。这种蜕变发生在他的内心,有一种几乎令人害怕的活跃。值得一提的是,泽农之所以留在布鲁日,除了需要照顾一些病人以外,与布鲁日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结下的深厚情谊也令他难以割舍,而院长同样需要泽农这样一个在知识和思考的深度上可以与他交谈的对象。
16世纪佛兰德斯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下,尤其是菲利普二世继位后,对佛兰德斯争取民族自决的诉求实行高压政策。院长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热忱的爱国者。对时局的共识,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让院长和泽农之间建立起深厚的默契和信任。
“医生也喜欢上了这些彬彬有礼却又几乎完全排除了谎言的交谈。尽管如此,他离开后却隐隐有一种欺诈的感觉。又一次,如同人们在索邦神学院只能讲拉丁文,为了让人理解,他不得不采用一门扭曲自己思想的外国语,尽管他娴熟地掌握这门语言的音调和措辞;……他们在院长的修室里长时间讨论的话题,在戴乌斯博士独处时的沉思中几乎没有什么位置,如果院长得知这一点,一定会非常吃惊。并非因为泽农对尼德兰的苦难漠然置之,而是他经历了太多血雨腥风,面对人类疯狂的这些新的表现,他不再像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那样深感痛切。”
这段话体现出作者对语言的思考。泽农认为,虽然他和院长都能娴熟使用拉丁语交谈,但这仍是一门扭曲自己思想的外国语。其实,任何语言对我们的思想都是一种扭曲,这与泽农即将在深渊中进行的对概念、语言的重新审视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泽农与院长的谈话也揭示了人际关系中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即便是在泽农和院长两位非常坦诚的人之间,也难以排除“谎言”和“欺诈”。此外,泽农面对眼前正在发生的苦难,并没有表现出像院长那样的痛切,这是因为他的内心深处,进行着更加深刻的思想的“黑功”。与院长讨论的话题在泽农独处时的沉思中并没有什么位置,因为另外的思考占据着泽农的内心。
他在济贫院的小阁楼里,重新检视一生中探究过的重要概念,无论这些概念属于观念世界还是属于物质世界。正如“黑功”是在坩埚中煅烧物质从而分离提取出更为纯粹的物质,泽农也尝试透过他所获得的概念去把握概念对应的事实。他通过各种方法来认识精神与肉体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试图检验自由意志是否受制于物质基础;他追忆往事,尽力分辨其中哪些属于自己作为个体的独特经历,哪些与生而为人的普遍境遇相关,他从自己的经历当中看到曾经营造的空中楼阁,也看到时代的疯狂和残暴……他曾经获得的概念坍塌了,甚至时间和空间的概念都发生了变化,物质也渐渐显露出它们的本质:
“一片森林占据了房间。这条矮凳是按照从地面到一个坐着的人的臀部之间的距离来制作的,这张桌子是用来写字或者吃饭的,这扇门将封闭在一个立方体里的空气向一个相邻的立方体里的空气打开,它们失去了某个工匠当初赋予它们的存在理由,就像教堂的油画上那些圣巴托罗缪一样,它们只不过是剥了皮的树干或树枝,上面还有幽灵般的树叶和看不见的小鸟,它们还在早已停息的风暴中簌簌作响,身上还有刨子留下的汁液凝结而成的颗粒。这条毯子和这件挂在钉子上的衣服,还散发着油脂、奶和血的气息。在床边敞着口的这双鞋,曾经随着一头躺在草地上的牛的呼吸而起伏,而补鞋匠涂抹在上面的油脂里,有一头被放尽了血的猪在轻声尖叫。如同在屠宰场或者执行绞刑的围墙里,残暴的死亡无处不在。我们在旧纸片上记录下那些自以为值得传之永远的思想,一只被杀死的鹅就在用来写字的羽毛里叫喊。一切都是他物:贝尔纳会的修女们为他浆洗的这件衬衫,曾经是一片比天空还要蓝的亚麻田,也曾经是浸泡在运河深处的一团纤维。他的口袋里有几枚铸有已故查理皇帝头像的金币,在他自以为拥有它们之前,它们曾经无数次被交换、施舍、偷窃、称量和克扣;然而早在亚当出生之前,金属本身已经与大地融为一体,与这种静默的存在相比,它们在那些吝啬或者挥霍的手中传递的时刻终究不过是过眼云烟。”
尤瑟纳尔的晚年回忆录《北方档案》(Archives du Nord)中有一章,题为《时间的黑夜》(La nuit des temps)。其中讲到,在她的祖先出生以前,甚至在人类存在于这个世界之前,地球上已经有了小鸟;在小鸟出现之前,天上的星辰便已经存在;我们如今在星辰之间连线,将之命名为大熊星座、小熊星座、天琴座等等,但这些星星已经在天上闪耀了数不清的年代,它们在天空中的闪耀与人类对它们的命名毫无关系。

尤瑟纳尔与自然
这也正是泽农在深渊中的思考,他意识到一切都是他物,一切都是过渡,包括人自身。泽农在深渊中完成了“哲学之死”:炼金术士既是炼金术的操作主体,也是被锤炼的物质本身,他从思想的腐烂、形体的扭曲中获得了经验,完成了精神的提升,感到自我“像风中的灰烬一样飘散”。从当年那个出发去寻找“泽农在此”的意气风发的少年,他变成了放弃自己名字的戴乌斯医生,以至于一天有人偶然问起他是否认识一个叫做泽农的人,他几乎不假思索就做出了否定的回答。
至此,泽农完成了他自己的“黑功”。
“大功的第一阶段已经耗尽了他的一生。就算有一条路,而且人可以从这条路上通过,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走得更远了。或许,这种思想的腐烂、本能的死亡、外形的扭曲是人的本性几乎无法承受的,经历了这些过程之后,随之而来的也许就是真正的死亡,倘若这样,他倒想看看究竟是通过哪一条路径;或许,精神从那些引起眩晕的领域回来之后,又会回到惯常的套路之中,只不过它所具备的官能就像清洗过之后那样更加自由了。倘若能看见这一切的效果该多好。”
其实,走出深渊的泽农,精神经过彻底的涤荡,不知不觉间已过渡到“白功”阶段:他的医术变得更加精湛,他为前来济贫院求医的穷人诊疗,如同从前为王侯们治疗一样,内心不再有任何野心和戒惧,他的专注里甚至没有掺杂怜悯。然而就在这时,修道院的一群年轻僧侣发生了为教会和世俗法律所不允许的行为,致使泽农受到牵连而被捕。他被捕时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使得案情彻底转变,泽农由一个放荡者小团体的无足轻重的从犯,变成一个极其危险的无神论者和渎神者。
小说第三部《牢狱》讲述了泽农在监狱里度过的生命中最后两个月。泽农对那些长篇大论的控告以及法庭上似是而非的神学辩论毫无兴趣,他甚至会在法庭上睡着。事实上,一个法官也在法庭上打瞌睡,这体现了审判的荒谬之处。而泽农当年的老师康帕努斯议事司铎认真旁听了审判的全过程,他无力拯救钟爱的弟子的灵魂,只能寄希望于拯救泽农的肉体。在泽农被宣判死刑的当天,他来到泽农的监狱,希望泽农能在最后的时刻悔过。泽农向司铎陈述了自己对自由的看法:“当年您向我传授文学和科学基础知识的时代,有个认罪的人在布鲁日被烧死,不知道他犯下的罪行是真是假,一个佣人向我讲述了他遭受的折磨,为了增加这出戏的趣味,人们用一条长链子将他系在柱子上,这样他浑身着火以后可以跑来跑去,直到扑倒在地上,或者不如直截了当地说,扑倒在火炭上。我常常想,这个可怕的场景所包含的寓意,就是一个基本上自由的人的状态。”
泽农对于人的自由没有虚妄的看法。哪怕我们不是囚犯,也总是被很多东西束缚。这些束缚也许是外在的,但尤瑟纳尔深刻意识到,束缚更多来自我们个人的成见,我们内心中墨守成规的一切,都是拴住我们的链条。
泽农没有告诉司铎的是,他拒绝司铎所许诺的自由,但他为自己保留了另一个巨大的自由——他要实施自杀,死于自己之手。这固然是一种自由,但是一种令人筋疲力尽的自由。
“对他来说,自上午判决宣布以来开始的某种死亡的盛典,随着他跟议事司铎的谈话结束了。他原以为已经固定下来的命运重新摇晃起来。他已经回绝的提议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仍然有效:一个最终可能说‘是’的泽农也许潜伏在自己意识深处的某个角落里,即将过去的夜晚可能会让这个怯懦者占上风。只需千分之一的机会就够了:如此短促的未来,对他已成定局的未来,竟然因此获得了一种不稳定的因素,那就是生命本身,而且,他在病人身边也观察到过这种奇怪的情形,死亡因此保留了某种具有欺骗性的不真实。一切都摇摆不定:一切都将摇摆不定直至最后一息。然而,他的决心已定:他不完全是从勇气和牺牲的崇高迹象,更是从某种外形笨拙的拒绝中看到这一点,这个外形将他整个封闭起来,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影响,也几乎隔绝了感觉本身。他在自己的结局里安顿下来,他已经是永恒的泽农。”
这种外形笨拙的拒绝,实则就是来自心灵的力量,是泽农在整个人生当中积聚起来的心灵的力量。
泽农的死不完全是“勇气和牺牲的崇高迹象”,因为他的自杀不是对基督教教义的挑衅,也不是基于某种抽象的原则。小说里,尤瑟纳尔两次写到泽农对当时因异端思想而遭受火刑的几位人文学者和思想家的态度。一次是在因斯布鲁克跟亨利的交谈中,泽农提到西班牙神学家塞尔维面临的危险,他坦言自己手中有关于血液循环的重要研究要做,不值得为了捍卫某一信条而被活活烧死。另一次,面对一个无神论朋友针对宗教的玩笑话,泽农一方面觉得这些讥讽不免浅薄,同时却暗想,“在一个为信仰而狂热的时代,这个人粗俗的怀疑主义自有其价值”。泽农选择自杀,是因为他处于一种不可接受的境遇之中,他不愿接受妥协。他曾经尝试过流亡英国,然而仅从布鲁日走到海边,一路上看见人类的愚昧和狂热无处不在,不免心生厌倦。他想,自己已经五十八次看见冬去春来,生与死已无关紧要,便不想再做逃亡的尝试。另一方面,对泽农而言,在布鲁日广场上的死亡是一种近乎猥亵的被围观的死亡,是毫无疑义的肉体痛苦。因此,泽农决定实施自杀。
小说末章详细描述了泽农在生命最后几个小时里的内心活动以及实施自杀的细节。就在泽农下定决心的同时,他的精神和肉体之间爆发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突:
“即将成为现实的消息似乎突然间在他身上触及到身体的理解力,将恐惧的份额分配给各种感官:他看到,感觉到,闻到,听到了明天集市广场上关于他死亡的种种细节。肉体灵魂原本谨慎地待在一边,没有参与理性灵魂的思考,这时突然从内部得知了泽农对它隐瞒的一切。他身上的某种东西像绳子一样断裂了;他的唾液干涸了;他手腕和手背上的汗毛竖了起来;他的牙齿打颤。他在自己身上从未体验过的这种迷乱,比这场厄运中的其他一切更令他惊恐:……直至那时为止从未预见过的风险向他涌来,它们很可能会妨碍他理性的出路。他朝自己的处境投以一瞥,就像外科医生在身边寻找工具并推算运气。……他密切关注着周围的响动和脚步声;万籁俱寂,然而与从前任何一次匆匆出逃相比,时间都没有此刻那么宝贵。”
尤瑟纳尔冷峻克制的笔触更加凸显了泽农之死的惊心动魄。接下来,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小说描写了泽农逐渐失去所有的知觉和感官:
“他再也看不见了,但还能听见外面传来的声音。如同前不久在圣科姆济贫院,走廊里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管钥匙的狱卒刚发现地上有黑乎乎的一摊水。就在片刻之前,垂死者想到自己可能会被抓住,被迫再多活和多死几个钟头,他也许会被一阵恐惧攫住。然而一切焦虑都终止了:他自由了;这个朝他走来的人只会是一位朋友。他做了,或者以为自己做了一下努力,想站起来,但是他不太清楚究竟是自己获救了,还是相反,是他前去搭救别人。一阵转动钥匙和推开门闩的嘎吱声,对他来说从此仅仅是开门时发出的尖利的声音。这就是我们跟随泽农能走到的最远的地方。”
这里的“自由”意味深长,指的是他自杀成功,结束了生命,摆脱了屈辱的死亡。“这就是我们跟随泽农能走到的最远的地方”是全书唯一一处使用一般现在时的句子:尤瑟纳尔从不认为死亡就是人生的终点。至于泽农要去到什么地方,则无从得知,我们能够见证泽农的故事到这里为止。
《苦炼》蕴含着丰富的启示,其中之一便是关于自由的探讨。尤瑟纳尔在《苦炼》的“创作笔记”中将泽农追求的自由与她笔下其他人物追求的自由做了对比:“沉思中的哈德良有时会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我们;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仍在使用的古代智慧的桥梁,也可以接近哈德良。《苦炼》里的人物只对他们自己负责,他们孤独,矛盾,既被他们接受的东西,也被他们拒绝的东西所限制,时代在他们身上打下印记,有时为了逃离这个时代,他们甚至不惜撞在囚禁他们的牢狱的墙壁上,然而他们要逃离的东西也在他们身上打下印记。”
年轻读者们往往对泽农或亨利早年离家出走追求自由的冒险着迷。其实,无论是我们接受的事物,还是我们拒绝和逃离的事物,都会在我们身上打下印记。尤瑟纳尔在1934年出版了一部名为《死神驾辕》(La Mort conduit l’attelage)的小说集,其中包含三篇小说:《仿丢勒》(D’après Dürer,《苦炼》的雏形)、《仿格里科》(D’après Gréco,《安娜,姐姐》的雏形)和《仿伦勃朗》(D’après Rembrandt,《默默无闻的人》的雏形)。《安娜,姐姐》中的主人公通过尝试突破禁忌来获得肉体的自由,而《默默无闻的人》的主人公则试图摆脱文明和语言的束缚,不借助词汇进行思考,以达到心灵的自由。
“《苦炼》试图呈现的是另一种奇异的自由,即如果我们不拒绝它的存在,它就在我们自身逐渐发展起来,使我们得以摆脱某些桎梏,使我们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都得以成为我们自己,即便习俗和必需已经让我们身受重创,变形,几乎扭曲。”
我们要逃离的事物在我们身上打下烙印,即使扭曲变形、深受重创,这仍然是我们努力要成为的自己,只是并非与我们之前所设想的完全一样。

《死神驾辕》法文版封面,格拉塞出版社1934年版
在深入解读小说文本之后,段映虹教授补充了尤瑟纳尔对历史小说的看法。尤瑟纳尔的主要作品往往被评论界冠以“历史小说”之名,但她本人并不赞成这种说法。尤瑟纳尔认为,哪怕是写当代的故事,她收集材料、描摹人物的方式也是一样,都是尽可能了解关于他们生平的第一手资料。她尤其不希望历史小说流于化装舞会,只是简单再现历史场景,而非深入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灵世界。尤瑟纳尔选取《哈德良回忆录》和《苦炼》的时代来创作,意在截取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时期,通过展示不同人物的命运和求索,表达对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的关切,为今人思考当下的现实提供参照。
在写作《苦炼》的几十年间,作家本人和整个人类世界的经历都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在尤瑟纳尔动笔写作《苦炼》的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阿尔及利亚战争正在进行。1968年《苦炼》出版时,正逢法国的五月风暴。这部较为艰深晦涩的作品竟然得到众多读者喜爱,并很快为尤瑟纳尔赢得巨大的声誉。泽农对现存价值观的反思与法国青年们对现存秩序的反抗形成对照,东西方铁幕的对抗也一定程度上在《苦炼》中新教与天主教的对垒中得到了投射。因此,尤瑟纳尔希望读者通过她的作品来认识那个时代,进而引发对于人类社会以及更大意义上的人类处境(la condition humaine)的反思。历经数十年,尤瑟纳尔终于完成了《苦炼》的写作,而这部作品也成就了尤瑟纳尔自己的思考。正如在《深渊》中,尤瑟纳尔写道:“二十岁时,他以为自己摆脱了使我们丧失行动能力和蒙蔽了我们理解力的成规或偏见,然而,他以为自己一开始就全部拥有的这份自由,后来却用了整整一生来一点一滴地获取。”
在写作《苦炼》时,尤瑟纳尔也许没有想到,在成书之后的1970年代,等待她的将是长达十年静止不动的岁月。由于个人生活出现的变故,尤瑟纳尔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出门旅行,她蛰居在一年里有五六个月都是冬天的缅因州荒山岛上。在此期间,她的精神世界也得到了全新的升华。她观察周围的事物,阅读大量的作品,其中包括她始终钟爱的东方哲学。在走出“静止不动的生活”后,尤瑟纳尔拥有了一种超越狭隘人文主义的广阔的宇宙观。她的作品越到后期,思想愈加深邃,语言愈加明澈。《苦炼》开篇,年轻的泽农曾对亨利说:“但愿有神明,让人的心灵能够包容一切生命。”(Plaise à Celui qui Est peut-être de dilater le cœur humain à la mesure de toute la vie.)这也是尤瑟纳尔的墓志铭。

尤瑟纳尔的墓碑
随后,段映虹教授对选课同学此前提交的《苦炼》阅读反馈进行点评。很多同学谈到泽农的自我实现过程,甚至称泽农为存在主义的主人公。对于二十岁左右的同学们来说,这种关注是自然而然的。同学们与离家出走时的泽农和亨利年龄相仿,同样都很期待在未来的人生中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但需要注意的是,泽农的自我实现需要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理解,泽农最后正是因为忘却了自己,才成为“永恒的泽农”。这也回应了泽农早年所说的“不仅仅成为一个人”。正如尤瑟纳尔的墓志铭所说,但愿人的心灵能够足够广阔,能够包容一切的生命。这种自我实现包含着泽农在深渊中对矿物、动物、植物的关照,对各种物质感同身受的同情,对更广阔的宇宙万物,而非人之为人本身的包容。

尤瑟纳尔在“怡然小居”(la Petite Plaisance)
尤瑟纳尔晚年曾作一篇文章,名为《院子里的沉思》(Méditations dans un jardin),记述她在蛰居生活中对自然的观察。她在院子里看到池塘边的青蛙,对它投以友好的微笑,希望在青蛙的眼里,自己和它身旁的石头无异;如果在路上遇到一只小狗,她希望自己被看作一根树枝。她不在意必须以一个人的形态存在于这些生物面前,希望世界万物都能相互友爱。这也和尤瑟纳尔晚年热心环保事业有关。她热心环保,并非只是为了保护所谓的“地球母亲”,而是因为她意识到,地球以及地球以外的整个宇宙,是远比人类长久的存在。因此,泽农的自我实现,不只是作为一个人的成功,而是对一个更广大的世界的认识。还有同学将与《苦炼》与黑塞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作比,黑塞作品中的两个人物所体现的更多是肉体和精神追求的对立,泽农则非常注重肉体和精神的关系。正如前面所讲,尤瑟纳尔的《死神驾辕》三部曲中,肉体、心灵与精神都交缠在一起,尽管这三种成分在每个人物身上所占的比例不尽相同。“在泽农身上,主要是精神占上风,然而也可以说精神被心灵持续不断的、几乎狂暴的冲动所激励,此外精神的提升也离不开肉体的经验,以及对肉体的控制。”尤瑟纳尔关注的,正是这几种成分的彼此交织和相辅相成。除了讲座中所提及的人物,也有同学关注到泽农同母异父的妹妹玛尔塔。从年轻时期的热忱到后来的保守与妥协,玛尔塔可谓走向了泽农的反面,也走向了年轻时代自己的反面。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和反思的人物。
讲座的最后,段映虹教授与选课同学进行互动交流。梁家瑞同学将泽农之死与苏格拉底之死作比,二人同因异端罪名受审,并在亲友劝说下仍执意赴死。某种程度上,二人都因为对自己哲学立场极度的坚持,而将死亡作为一种自我完成的方式,只是二者思考的方向有所不同,泽农更期待自杀为他的生命找到出口。李昕芮同学提出,泽农这个经过一生的求索,对宗教怀疑的人,在最终却达到了基督教对人守贫、禁欲、行善的要求,但实际缘由却与宗教无关,是泽农意识到一切都是外物,只有精神完全属于自己。李松晓同学谈到,哲学思辨性和宗教色彩使这本书的阅读过程十分困难,正面呈现出的情节仅仅是冰山一角,背后蕴藏着16世纪复杂的背景、宽广的地域、泽农那些未讲述的漫游岁月,无数曾发生过却没能被记录的故事湮没在时间里。段老师回应,自己在译书的过程中也不断感叹尤瑟纳尔笔法细腻,整部作品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不只是16世纪的很多事件,哪怕是泽农的一生,都经过了尤瑟纳尔的悉心选择和呈现。陈靖泽同学谈到作家所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以及面对死亡的淡然态度,段老师进一步补充,尤瑟纳尔不仅崇尚老子和庄子,也同样喜爱孔子。作家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名为《万物的声音》(La Voix des Choses),是她对自己一生当中热爱的句子的摘录,正是这些断章给予她勇气、力量和灵感。其中有不少来自老子和庄子的引文,可见尤瑟纳尔确实非常熟悉道家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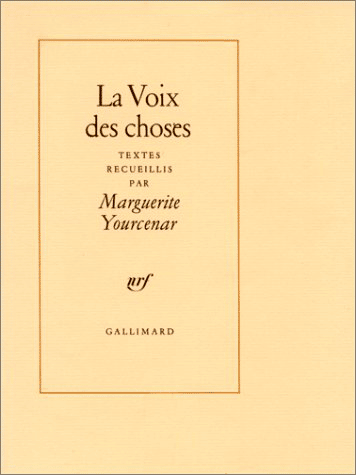
《万物的声音》法文版封面,伽利玛出版社1987年版
尤瑟纳尔面对死亡的态度也并非独创,她所喜爱的蒙田也持类似态度。蒙田认为,人们每天都在掉头发,年老之后还会逐渐掉牙,这都是死亡的一部分。死亡不是一个突然到来的事情,而是一直都在进行的缓慢过程。郝元隆同学认为,《苦炼》的第一部试图为中世纪覆上一层清漆,它照亮了小人物的生活,暗示了历史的复杂褶皱;第二部开始从泽农的视角出发,从细节处关照整个生活,两个温情的角色——慈爱的格利特与包容的院长为小说增添了温度。尤瑟纳尔在《作者按语》中梳理人物和事件在历史中的来源,揭示了小说的创造性在于对不同经验间关系的发现和建构,这样的经验可以是历史的,也可以是个人的,而新的意义亦在被塑造的经验之中呈现。段老师回应,格利特和院长确实是两个有意思的人物。格利特认出泽农的情节,似乎是在向《荷马史诗》中尤利西斯的返乡情节致敬,而院长的包容可用泽农的一句话概括——“我们在矛盾之外相会”。

编辑:吴辰宣
以下为本站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