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像自杀
第一次来巴黎求学,我住卡门公寓,出门左走二百米,是著名学者巴特的祸地,路边的“学者屋”储了些说法。公寓靠近塞纳河,邻圣母院,从我的窗口,可以看见密特朗的私宅。那一站的地铁叫Maubert Murtualité。刚来时,我对巴特一无所知,公寓的女经理却是巴迷,在接待间,她摆了六七本巴特的书。那日得了闲,我取出《符号帝国》,读几行,立刻被吸引,择译如下:“满满一桌菜,你伸出筷子,常常无定数,须指一指,游一游,再落定某一盘,那里有东方的随意。拿木筷捻嫩豆腐,力大了碎食,劲小夹不起,松紧之间,含了中庸之道。我们的刀叉更具侵略性,它叉切捣碎,明目破坏,张胆野蛮,步骤机械,动作单调。”

女经理早已感出我的兴奋,添油提议:巴特才走两年半,在这一带留了些气息,有空去一去学者屋,那曾是巴特常去的咖啡馆,老板酷爱文学,与他厚交,知道许多可贵细节。我非常想去,却没立刻成行,原因说出来挺丢人的,我舍不得花那三四个法郎。1982年春,我刚留校任教,月薪54元。半年后到巴黎,奖学金高达2800法郎,相当我五年的工资,四法郎够我在川外吃五天带肉的饭。仰望圣母院,我常常自诫:能节则节,能省就省,天上一日,地上一年。
两个月后,我找到一个丰润周末工 —- 推销香水。那时巴黎的中国人不多,因法语流利,远东的面孔帮了我的大忙。某一日,我远远超额,得了200法郎奖金。我又自语:意外之财额外花,你留出四分之一,专项喝咖啡。已探明价位,连带小费,50法郎可喝10杯拿铁。翌日十点整,我走进学者屋,坦然奢华。问起巴特,聊几句,立马勾住老板。我细读了巴特五本书,有些见解。老板惊叹:没想到中国人也有热爱巴特的,周一比较闲,你若有空,三点来,我们在此详谈巴特。我一个劲点头。

回去后,我认真阅读《巴特自述》,原文叫 Roland Barthes par Barthes。那是巴特写的一部自传,用第三人称,由片段组成,许多段落才三四行,突出读书心得与碎片思考。开头登四十多张实景实人照,解说空灵隽永,诗意盎然。后附一则简要生平,译成中文千余字,主打名词句,只写到1962年,末尾在括号里归纳:他的一生:学习,疾病,任命。其余呢?诸多会见、友谊、爱情、旅游、阅读、欢乐、害怕,还有复数的信仰、享受、幸福、愤怒、悲伤,一句话,都是文本中的反响,而非著作。)
那个下午,学者屋没营业,偌大个堂,只老板一人。桌上备了三种糕点,招待很隆重。我有备而来,呈送一套剪纸,老板打开,眉飞色舞,当即贴出一幅,远近看两眼,赞不绝口。又倒两盏香槟,碰个杯,娓娓开讲:1980年2月25日中午,密特朗在家中宴请巴特,大谈符号学,众乐融融。结束后,巴特赶回学校,刚到学者屋,被一辆小货车撞倒。救治一个月,时好时坏,索莱尔斯、克里斯蒂娃、福柯等好友常去看望,终因肺部感染,撒手人寰,享年65岁。媒体异口同声:法国失去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位文学批评家。我悲痛了好一阵。出事那一刻,我恰好看见,巴特穿一件浅黄色外套,埋着头,直往前冲,有点像寻短见。人行应该是红灯。被撞后,他在路上滚一圈,沉入昏迷,脸部在抽搐。司机扶守伤者连连说,是他冲上来的,是他冲上来的。我回店打电话,来了救护车。多人出面作证,当局没有追究司机的刑事责任。

我紧锣追问:说巴特自杀有什么根据?老板答:根据谈不上,却有三大可能的理由。第一,五年前,母亲去世对他打击太大,对我,就在你身后的桌子旁,他曾三次说,最亲的人走了,天昏地暗,不想久待了。第二,在法国的最高讲坛,他开了一门课,叫“小说的准备”,越讲人越少。许多听众说,他啥都讲,比如摄影、时尚、暗房,微笑,红酒,邮票,就是不讲写小说该准备些什么。
我欣欣插话:虽为纯学者,巴特一直想写一部好小说,想法太多,一筹莫展。《情人絮语》是个可贵尝试。好友杜拉斯却在读书节目上骂了他几句,说他满脑条条框框,压根不知什么是纯写作。他对自己产生怀疑,出现了某种危机。老板说:是这么回事,巴特长于片段写作,优于鳞闪,同时又看到,传下来的杰作都有一定的连贯性,简单的说,好小说要有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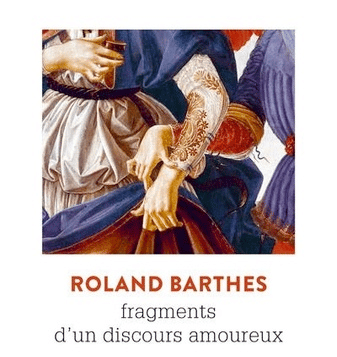
也许话题太深奥,老板停下,喝几口香槟,理理头绪,继续论说:故事太连贯,又会封闭文本。“作者之死”乃巴特对文学的一大贡献,依其之见,语言包罗万象,体系强大,作者只是其中的小小演员。写作时,往往语言在主笔。一旦发表,作品的权威是读者,我们无需一味追寻作者的意图。应该让文本说话,缤纷意义,文学的高层价值在于见仁见智。我索源解说:作家之死也得益于东方艺术精神,在日本俳句中,巴特发现以少胜多的智慧,体会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魅力。日本取了华夏艺术观,巴特的零度写作受惠于我国的留白。
老板欢叫:此刻中法交合,波光粼粼,美景多多。另一面,巴特立足西方的求实,片段,他写得挺精彩。老板翻开《巴特自述》,朗朗开读:“B先生是个小老头,教高一A班,爱国,信奉社会主义。年初,他站在黑板前,庄重统计为国捐躯的英烈。黑板上列出的都是舅叔堂表兄之类的,只有我一人说的父亲,有点局促,那是一个极端的印记。黑板擦去,悲哀消失,却实存于我的生活之中,现实的痛苦常常沉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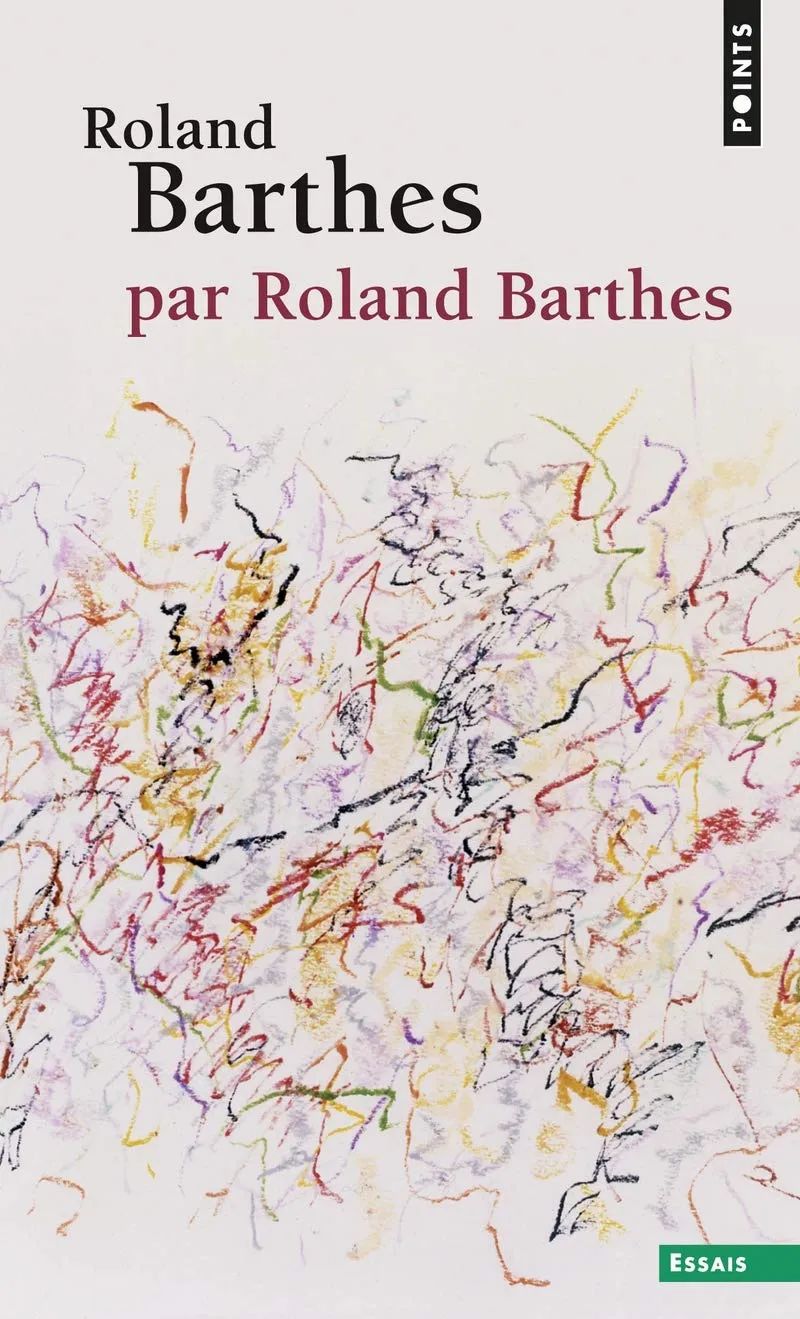
音落意未尽,又翻到开头,朗读第一小节:“他写的东西,分两个类型。文本I消极,或称反作用,充满愤怒、恐惧、反击、妄想、自卫、争吵。文本II积极,以快乐为主导。为了应从某种风格,写着改着,文本I变积极,失去了反作用,消极只得零星存活(现于某些括号里)。” 这一段可谓全书的纲领,行文独特,常读常新。我热烈鼓掌,真诚叫好。
老板喝一口矿泉水,歇片刻,说起巴特有可能自杀的第三条理由:现在都已知,巴特是同性恋,他外貌堂堂,风度翩翩,在爱场里,却挫折多于欢畅。他爱的,难得到。得到的,持不长。好多围着他转的小伙子只想弄他几个钱。巴特常带伴侣来这儿喝咖啡,是驴是马,我一眼看得出。而他每一次都真诚,受了骗,还真诚。对他打击最大的是记者兼作家的吉贝尓。此君比巴特小40岁,也恋同性,与福柯同志多年。想在某刊发一篇文章,巴特答应帮忙,却附一个条件,文章刊出后,两人睡一觉。吉贝尓嫌他太老,没答应。巴特猛然看出自己的卑微,再受沉重一击。出事前一周,他苦苦对我说:弗洛伊德的原动力在我这儿熄了火。

最后谈到中国。1974年,巴特与索莱尔斯、克里斯蒂娃等四人应邀来到北京,团友情激心欢,面对乱坠,满眼天花。巴特冷眼旁观,独绪思索,看出了萧杀。他在日记中写道:“七八亿人,衣着呈三种颜色,灰、篮、绿,或者黑。从北京坐火车到湖南,一路的油菜花,除了油菜花,还是油菜花。嘤嘤嗡嗡的官员们只会说两句话:中法友谊万岁,瘟化大革命好。” 那日登上万里长城,大伙高唱赞歌,巴特却道,这也是自我封闭的象征。我应时补充:多亏邓小平,我们已改革开放,国家日益健康,生活走向美好。老板兴奋收尾:这样好,这样好,从中国回来,巴特在我这坐了两小时,反复说,哪能荒芜,灿烂的华夏应该有绚烂的当今符号。
—- 杜青钢,2022年6月2日。

